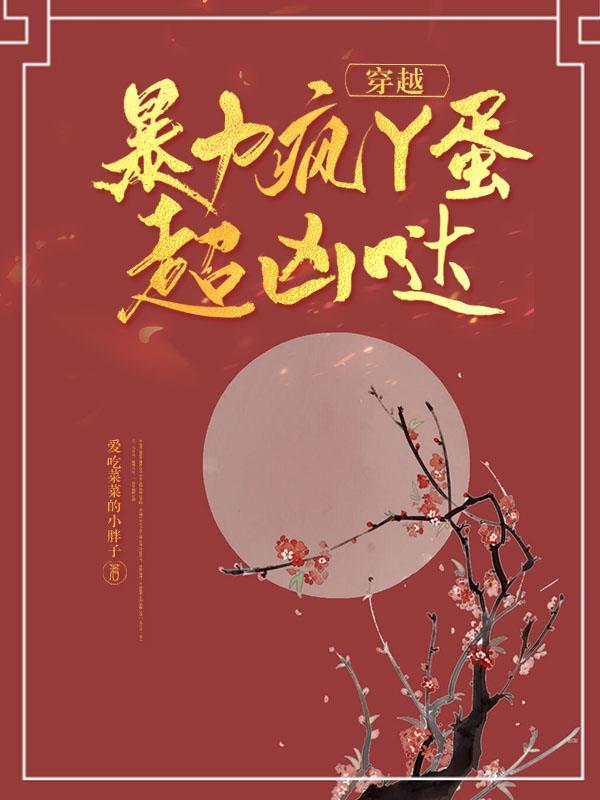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沾洲叹by诗无茶免费阅读 > 第89章(第4页)
第89章(第4页)
那边柳藏春得知自己也受邀前去冬猎,自是答应下来,欢欢喜喜地带上了自己的小猫。
上次马车里剩的山空燃完了,停驻的当儿,疏桐正躬身进来添香,听见车下动静,忽侧身一看:“柳先生?”
“疏桐姑娘好啊。”
柳藏春左手抱着猫,右手端着碗,满面春风地对着疏桐笑。
疏桐赶紧让开。
柳藏春一溜烟钻进车厢,贺兰明棋正支颐靠在小几上,撩起眼皮扫了他怀里一眼,心想:“小黑猫。”
“贺兰姑娘,”
柳藏春挤到贺兰明棋身边,腰侧的白月玉佩与矮榻相撞,出叮咚声响,他放下猫,改双手捧碗,“燃香再好,也忌讳多闻呢。”
车外疏桐看看自己手上还没拿进去的山空,暂时地静止了。
贺兰明棋沉默一瞬:“不点香,头疼。”
“头疼,是贺兰姑娘健想多思的缘故。心不静,则气性大,肝火旺,神思烦忧,自然颅内受感€€€€”
贺兰明棋做了个打住的姿势:“别念经,头更疼了。”
柳藏春收了话,把碗递过去,笑眼弯弯地说:“喝点安神汤吧。疏肝健脾,解表散热。食疗总比闻香好。”
贺兰明棋睁眼凝视着那碗乌黑的汤药,心里估量着自己不接药柳藏春继续念经的可能性,未几,还是接了过去。
疏桐听着个中动静,默默抱着香退下了车。
柳藏春送完药便很自觉地离开了,临走时像是故意把猫遗忘在车里,依旧是一副很和气的模样:“那我就不打扰贺兰姑娘休息了。”
说完便只身下了马车,留下贺兰明棋和那只半个小臂大的黑猫面面相觑。
贺兰明棋看着它身型不大点,毛却是是油光水滑的样儿,便知贪名赫赫的柳藏春把平日里赚的大把银子都用在了谁身上。
果不其然,那黑猫在马车里跑了一圈,眨眼功夫便将桌子食盒里的鱼肉点心还有水果搜刮得一滴不剩,最后试试探探地趴在贺兰明棋旁边,怯生生扒拉着她的袖子,见她没反应,便大着胆子钻到她怀中蜷缩着打起盹来。
贺兰明棋垂眼看着这只猫,心想:“小醉雕。”
于是她更烦柳藏春了。
这个人的烦,是不动声色、暗度陈仓的烦。烦得润物无声、无孔不入。烦在细枝末节,烦出了一种和贺兰明棋之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隐秘感。
柳藏春下了马车之后又去寻找祝神。
祝神眼尖,老远瞧见他朝这边过来,当即拉着容晖回了车厢,等柳藏春来打招呼时,只叫刘云托辞:“舟车劳顿,二爷身体不适,现在正睡着,柳先生到了行宫再行诊断吧。”
柳藏春低头一笑,对方这伎俩拙劣,可见祝神是故意敷衍,摆明了就是不愿意让他看病。他不点破,也不硬闯,只从身上掏出一个香囊:“这药囊是我自己配的,先前粗浅看了看祝老板的表征,便抓了些养神益气的药材。贴身带着,总归无害。”
他仁至义尽如此,祝神自然不好推辞。刘云拿了药囊进来,祝神便也安安分分地贴身放了。
北方冬夜严寒,不适合驻扎,他们一路抵达行宫,各自入住后,天也快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