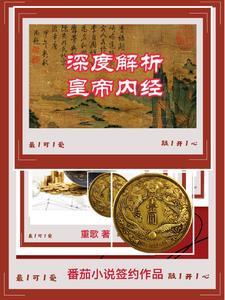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回到1973香朵儿 > 第50章 听梁教授讲座(第1页)
第50章 听梁教授讲座(第1页)
三人从南塬回到牛棚。
坐定后,梁家骧感慨道:“罗连长对村子的情况了解的蛮清楚的嘛,不用我们到处乱窜,就很快找到了合适的窑址,可为老夫节省了不少时间。”
“从小在山沟长大,哪个地方山高,哪个地方草多自然知道的多点。”
罗晓光嘿嘿一笑。“不过梁教授,没想到烧个砖还挺麻烦的。”
梁家骧也笑道:“这才哪儿跟哪儿。今天我们做的只是选址工作。这建窑的地方一般应选择在有沙土的河边,周边还要有一块平整的场地。这平整的场地是留作以后‘摔砖坯’用的。你看土丘周围的大片灌木丛,砍伐平整后是不是就是一块很好的‘摔砖’场地?”
“还是梁教授厉害,半天功夫就把窑址敲定了。”
罗晓光夸赞道。
想到大哥对砖瓦窑还是零概念,纯粹的一个外行,以后要管理这个窑厂,显然是不行的,现在应该对他进行强化培训。
“梁教授,我大哥对砖瓦窑的建设及制作流程还不是太了解,你能不能先给他讲讲,让他有个大致的概念,然后再慢慢摸索,也好为他以后管理打点基础。”
“这没问题,你们千方百计为村民着想,为社员们谋福利,我老夫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太应该了,”
“那大哥你先在这和梁教授唠一唠,我回去让娘做几个菜,咱们晚上就和梁教授在牛棚喝上几杯,庆祝一下选址成功。”
“哎!”
罗晓光愉快的回应道。
方明站起身就走,梁家骧拦了一下没有拦住。
走了没几步,方明又回过头道来:“我快去快回,来了我们一起听梁教授给我们讲座。”
方明走后,“罗连长……”
梁家骧刚叫了一句,正要往下说,便被罗晓光打断了:“梁教授,你是个大教授,我只是个小社员,可不敢这样叫,我这个小辈哪能承受的起,就叫我小罗好了。”
没想到这罗家的人还都有理有面。看着五大三粗,说话倒挺客气。对罗晓光便有了几分好感。
别看这个梁教授整天不出牛棚,但对村子里的事,不能说了如指掌,但也掌握的差不离。当然,有时候和罗洪奎聊天,罗洪奎会告诉他村里一些新鲜事。不过多数情况下还是吴老栓提供的信息。
吴老栓每天赶着牛车,拉人上镇上办事购物。车上多是妇女,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嘚吧嘚吧。每次吴老栓的耳朵都被灌的满满当当,什么村中要闻了,家庭趣事了,吵嘴打架了,内容覆盖向阳寨的方方面面。
回到牛棚,吴老栓会把听到的内容全都掏出来倒给梁家骧听,梁家骧又很会分析概括,所以,对村子主要家庭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罗晓光就属于梁教授眼中的主要家庭,他的情况梁家骧自然掌握不少。
“小罗最近遇到烦心事了吧?”
既然不让叫连长,梁家骧便改了称呼。
这也能看出来?下午那会刚来牛棚的时候,不用方明介绍,他就知道自己是谁,现在又能看出自己还有烦心事,难道这个教授是个神仙,还会算卦?
“哦!家庭小事,不值一提。”
“家庭无小事,小事处理不好就会变成大事。”
梁家骧一脸严肃:“你妻子是个贤惠善良的好女人,不但在向阳寨,我敢说在红旗公社也找不出这样的孝女。这样的好女人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
梁家骧是有感而。
他因写错关键字被下放到向阳寨,本来就心灰意冷,感到孤单无助。妻子不但没有宽解安慰,反而是雪上加霜。由于忍受不了世人的白眼,又不愿背着坏分子老婆的名声,便割舍了几十年的夫妻感情提出了离婚。
屋漏偏遭连阴雨,梁家骧痛不欲生。当然,他谁也没告诉,村里人就更不知道了。
所以,当他听到罗晓光的妻子被母亲虐待多年,母亲要与女儿断绝关系时,本应高兴的女儿却悲恸大哭。
明知亲娘有大错,却仍不愿失去她,还要赡养她。梁家骧便觉得这个女人的孝心感天动地。认为完全可以搞一个新二十四孝图,把这个案例收入其中。
“这个教授太厉害了,怎么对我了解的如此透彻,也难怪方明和教授的关系走的这么近,原来都是有本事的人。
这难道就是古人所说的近朱者赤吗?那我以后也要常常登门,来这儿听梁教授谈一谈,说一说,努力变成赤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