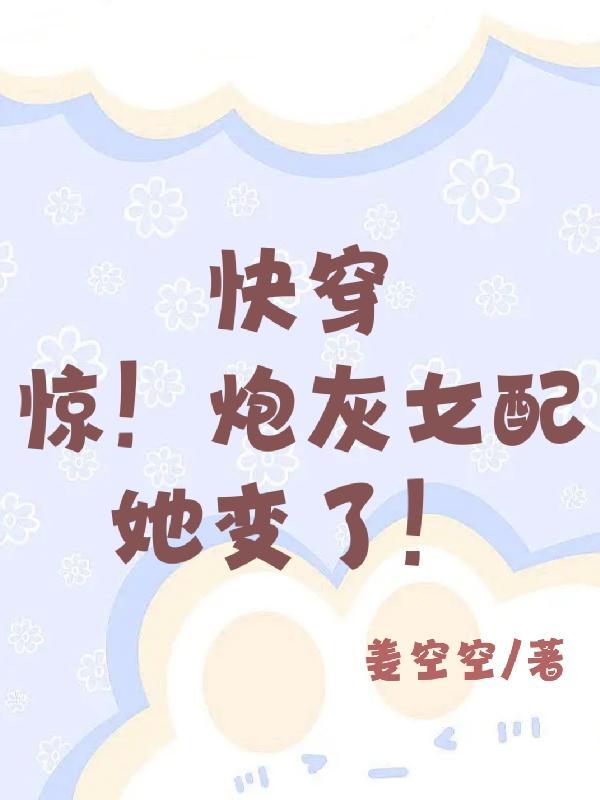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我和我的冤种朋友陈百强 > 第74頁(第1页)
第74頁(第1页)
沈君頤不說話。
安謹言就那麼等著,握著信封的手越垂越低,最後,他把信封丟在地上,定定地看著沈君頤。
「想好了來找我,是留是走,我都跟你一道。我等你三天,三天之後還想不好,就當咱倆從來沒認識過。沈君頤,人得自己給自己找活路,而不是指望活成別人的念想。」
地上有水,信封慢慢洇濕、軟塌塌地陷下去,像極了一個窩囊無用的承諾。
*
我最後一次見到沈君頤和安謹言,是在政商案開庭審判的前一天。他們辦好了簽證,馬上就要離開這裡。於是我們相約,再在墓園裡見一面。
沈君頤看上去氣色好了些,這人只要一活泛,那股自矜又算計的勁兒就又起來了。於是我忍不住諷刺了一句:「喲,準備好過苦日子啦?」
沈君頤笑了笑,沒接茬。只是百感交集地說:
「我一直覺得6游挺糾結的。」
「嗯?」
「都死去元知萬事空了,最後還是要家祭無忘告乃翁。萬事空就是萬事空,告一萬遍,其實寬慰的也只是後人自己而已。」
墓園寂靜,陽光暴烈。遠遠地,我們看見有個男人的身影,佝僂著穿過林立墓碑,來到沈君頤師傅的墓前,從塑膠袋裡掏出幾樣供品,恭恭敬敬地擺在墓碑前。
「那是誰?」安謹言朝那方向抬了抬下巴。
「不知道。以前他哪個當事人吧。」
「所以,寬慰的也不只是你們這些後人呀。」安謹言說,「是所有為了生活、為了某些心愿,不得不妥協、不得不苟且,跪著等很久很久,也要看到結果的人。」
松林如濤,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沈君頤側過臉去,注視著他的小愛人,兩人悄悄碰了碰手指,然後悄悄牽住了手。
作者有話說:
沈律和小安的故事就到這兒啦。其實寫到後面有點遺憾,因為如果展開講,關於案子,關於沈律的好與壞,原則與圓滑,堅守與完成後的幻滅感,可以寫很多很多。但這勢必就要牽涉到一個問題——究竟要怎麼寫這個案子。
寫著寫著就覺得。。。算了,讓小說歸於小說,意難平歸於意難平。
故事的主題就是妥協吧。年輕的時候總覺得人生就應該黑白分明轟轟烈烈,寧為玉碎絕不妥協。長大後才發現,妥協才是生活中的大多數,也是達成最優解的最好方法。
而有一類妥協是值得尊敬的——明明是個驕傲,寧願玉碎的人,卻願意為了某種信念、某個人,實現某個遠大的理想,去退讓和彎腰妥協。
就沖這點,雖然很討厭沈君頤,但最後還是給他一個好結局吧
第五卷蜉蝣
第57章蜉蝣
1。
很多年前,一個朋友跟我說,不要把感情的話題留在深夜裡談。因為深夜往往是一個人最脆弱的時候,這時候如果隨便跟固定某個人聊天,很容易把排遣寂寞誤認做愛情。
我記住了這句話。因此從不在晚上聊感情。但我有個隱秘的惡味,就是在晚上聽別人聊感情。
「調頻93。6兆赫,各位聽眾朋友們晚上好,歡迎收聽《春和夜之聲》,我是春和……」
今天下班比較早,我很累,於是打車回家。在車上,司機隨手打開了車載廣播,熟悉的背景音和旋律就汩汩地流入耳中。
春和緩緩地讀著一封投稿,那是寫信的人在深夜裡的懺悔與追憶。他說自己曾愛過一個特別好特別好的人——不僅僅是俗世意義上的完美戀人,而是一個近乎聖人的人——為了一個承諾,大學畢業之後,執意去一個特別偏僻的山區支教了五年。
「而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普通的家庭,以及普通的良心……」春和淡淡地讀著,深夜將他的嗓音染上一分天然的撫慰感,不管是什麼樣的內容,被他讀出來,總有一種哀而不傷的意味。
「……很多年之後,當我什麼該擁有的一切都擁有了之後,我總會想起那些單純、熾熱的日日夜夜。於是懊悔,其實,我們這樣的人,還有什麼未來可言呢?既然如此,等他一天,一個月,和等他五年,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回來的那天,京城下了好大的雪。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他,跟他說,你還記得嗎,我第一次看雪也是跟你一起,那會兒我還是個從南方來的土包子,看到雪會激動得歡呼,你就笑話我,教給我你們北方孩子會在冬天玩的遊戲,打雪仗,坐冰車,滑冰,騙我舔冰溜子。這些年來,每到冬天,我都很想他,我想說你知道嗎,賓夕法尼亞的雪很大,比我們當年一起經歷的每一場雪都大,我拍了很多照片,始終沒有勇氣發給你看。」
「我就這樣,弄丟了我愛的人。」
音樂漸漸低了,春和也收了聲,靜靜等著音樂尾聲結束之後,便可進入下一段。我猶豫了一會兒,打開微信對話框:
「春和,剛讀的那個來信,能幫我問問聯繫方式嗎?」
音樂結束。插進來一段廣告,同時響起的還有我的手機鈴聲。「餵?」
「餵?景明。八百年不聯繫,一發消息就是跟我要聯繫方式啊?」
「……」
「採訪嗎?」
「……嗯。可能吧。」
「你現在都做這類題材了?」
「也不是。可能試試吧。」
「我問人家一下,人要是同意就發給你。最近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