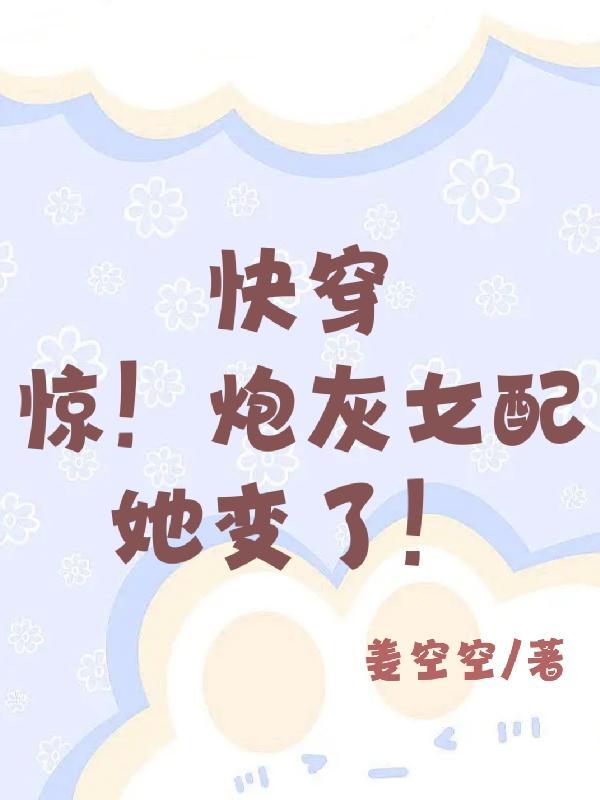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我和我的冤种朋友们电视剧免费观看 > 第45頁(第1页)
第45頁(第1页)
然後就線下見面,詩壇明星碰上傳媒秀,一眼定情緣。
凡姐說她至今深深懷念著那個時候的韓放,韓放是個有點內斂的人,也不太會應酬,但跟她總有無窮多的話。兩人談戀愛那會兒,經常通著話就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才掛斷通話。韓放依賴她,也撫平她,因此當韓放向她求婚時,她沒有任何的驚訝與猶豫,就像是百川終會歸海,韓放終會向柳思凡求婚,這都是順理成章的事。
只不過詩壇明星終究是曇花一現。文化界比媒體界更講究論資排輩、互相抬轎子。有一次,韓放被推薦參加一個獎項評選,有前輩指點他,說最資深最有分量的評委很看好他,他只要稍微表示表示、拜拜山頭,大獎非他莫屬。但韓放不屑一顧,私下裡說,他有什麼作品啊?不就是靠「研究」那幾個大佬的作品出名,人家寫文學批評那是解析批評,他寫文學批評那是變著方拍馬屁。就這人還好意思跟別人要錢。
不知這話是不是傳到當事人耳朵里,總之,韓放落選了。
這種事一次兩次還好說,多幾次之後,漸漸地,也就沒人再願意抬韓放的轎子了。因為在大家眼裡,韓放就是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還總愛戳破圈子裡一些眾所周知、卻又不好公之於眾的潛規則。
既得利益者正襟危坐,誰願意被「不識好歹」的人掀開老底,翻出通紅的猴屁股呢?
於是韓放這顆星變流星,就這麼迅地划過當代文壇,隕落得無聲無息。
但凡姐無所謂,用她的話說,兩口子過日子,只要自己覺得配合得當就行——其實外人看來他們的確是良配,女主外男主內,凡姐在外面混得風生水起,韓放則兢兢業業地當著講師顧著家,把老的小的照顧得井井有條。連凡姐在國外交流那半年,家裡老母親拆遷換房,都是韓放一手打理出來的。
「所以我就覺得——韓放對現在的生活到底還有什麼不滿意呢?吃穿不愁,有車有房,錢也沒讓他操過心。我們也不是那種忙於事業疏忽交流的中年夫妻,我的確不理解,到底還有什麼不滿意呢?」凡姐啜了一口啤酒,幽幽地說。
「那天去見那個小女孩,她說是跟韓放聊文學聊上的。那一刻我真的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我就想,你老婆不會聊是嗎?你老婆不僅科班畢業學文學懂文學的,還是個專職的文字工作者,還是獲過獎的文字工作者,怎麼著,滿足不了你的精神需求了?非得找小姑娘聊才能獲得精神共鳴?」
我深深地看著凡姐。她連落寞都是美麗的,連發牢騷都是優雅的,可是她這般通透,在這件事上還不是身在局中,霧裡看花。
男人,就是一種既要又要還要的生物。他們想要一個又美又有情還能掙錢的伴侶,但又不希望伴侶風頭太盛蓋過他們。凡姐什麼都能包容,包容了他的清高執拗,也包容了他世俗意義上的失敗;她什麼都能給韓放,家,錢,愛情,但唯一不能給他的,就是那種雄性生物與生俱來的尊嚴。他的才華、能力和弱點,尤其是一次次的打擊,都被自己的妻子所見證。他只能隔著網線,從小姑娘那裡得到一點虛幻的仰望。
一時間,我竟不知道凡姐和韓放,究竟誰更可憐。
第36章
11。
那晚我跟凡姐喝著酒聊著天,一直聊到晚上十一點,突然,頭頂白熾燈閃了閃,倏地熄滅了,連帶著嗡嗡作響的空調也一併啞了。
「停電了。」我倆在黑暗中等了一會兒,見沒有來電的意思,凡姐摸到牆邊按了幾下開關,「你今天工作都做完了嗎?」
「嗯,我這邊完了。」我說。
「我也完了。那不等了,咱走吧,明天打個報告補打卡。」
我倆打著手機電筒,順著樓梯一圈圈往下走。樓梯間真黑啊,集團晚上值班的人不多,凡姐的高跟鞋敲擊在瓷磚地上嗒嗒響。其中有幾層在裝修,裝修材料堆在樓梯間,我不得不在前面先探路,讓她跟在我後面下樓。
「得虧有你。我可怕黑了。」凡姐一邊小心找地方落腳,一邊跟我說話。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突然從腳下傳來一個氣喘吁吁的聲音:
「思凡?」
我擎著手機往下照,另一束手機電筒的光從下面一層打上來,是韓放,他一手撐著樓梯扶手,一手舉著手機,狼狽地推了推眼鏡,朝上看了過來。
見是我,他收了手機再度拾級而上。我抬頭看了看牆壁,上面貼著一個大大的數字「九」。我們辦公室在第十九層,我跟凡姐從十九層下來,而韓放,則從一樓爬樓梯上來。
「謝謝了啊,蘇老師。」畢竟是三十五歲的人了,一口氣爬九層,韓放有點喘,他連氣兒都來不及喘勻就轉向凡姐,溫柔又有點嗔怪地說:「怎麼不接電話啊思凡?我還怕你不敢下樓。」
兩個人一上,一下,隔了整整半層台階。凡姐低頭俯視著她的丈夫,她的身形隱於黑暗,而臉卻在韓放的電筒光之內,濃密的的長捲髮像一道帷幕,遮住了小半張臉,莫名地,讓她看上去像是馬上要變成泡沫的美人魚。
沉默對峙了一小會兒,凡姐輕輕地說,沒看手機。
於是我們仨就一齊朝樓下走去。
很快我就後悔了。早知道韓放來接凡姐,我就該呆在辦公室里等來電。因為等走到一樓大廳的時候,凡姐走在最前面,我緊隨其後,韓放在最後,凡姐剛一推開通道門,我就聽見一個聲音喊:「阿凡!你怎麼不接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