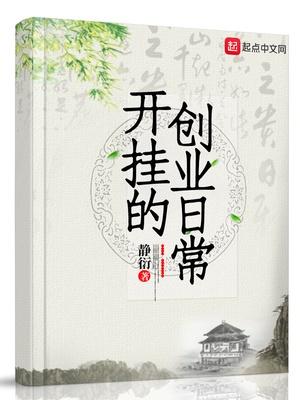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我和我的冤种朋友们电视剧免费观看 > 第17頁(第1页)
第17頁(第1页)
可是雲想濤的衣角已經消失在安檢門的另一側。
我說,非凡老師……人已經進去了……
趙非凡還是來了,在四十分鐘以後。你永遠不知道京城的交通會在什麼時候堵在哪一段,但毫無疑問,至少這一天,它堵在了趙非凡挽留愛情的最後一寸。
掛了趙非凡的電話,我緊急給雲想濤發消息,想讓他再多等一會兒,哪怕一刻也好,但消息發出去,是一個大大的紅色驚嘆號,雲想濤決絕地,在跨過安檢門之後刪掉了我。我又急忙跑到廣播站去廣播,然而「雲想濤先生,聽到廣播請到安檢處,您的家人趙非凡先生正在找您」響了一遍又一遍,那個身影卻再沒有出現。
最後,是趙非凡踩著廣播聲,撥開人群,滿頭大汗地跑來。我不敢直視他殷切的眼神,於是別開目光。不過我想趙非凡應該早已想到這個結局,畢竟他才是最了解雲想濤的人。他跑到我身旁,沒有問我是否攔下雲想濤,沒有問我雲想濤留了什麼話,只是一把緊攥住我的胳膊,從喉間擠出一聲響亮的悲泣。
玻璃穹頂外陽光暴烈,有飛機從我們的頭上越過,奔向廣袤天空。京城機場每天起飛八百架次,不知哪一架次載著他的愛人。
第15章
26。
兩周後,趙非凡突然叫我去幫他搬家。
說來狗血。在機場,我把那張銀行卡給了他,他不發一言揣了卡就走,絲毫不管我這個被無端卷進其中,被動當了傳話人的倒霉鬼。我一溜小跑跟在他身邊,看他一腳油門直接踩回他們之前那個「家」所在的小區。
他們的房子很好賣,雲想濤掛出去沒多久就賣掉了。那天下午,趙非凡賴在中介那兒,好說歹說,把剛拿到鑰匙三天的買家給約了出來,又用了四個小時的時間,以高出雲想濤售價二十萬的價格,把房子買了回來。
那位買家一開始並不想賣,但被趙非凡密集的語言炮彈轟得實在不耐煩,最後像送瘟神一樣鬆了口。
憑空淨賺二十萬,買家臉上不見喜色,在經歷了兩周內光買房過戶再光賣房的魔幻經歷後,他的臉上滿滿當當寫著「這人有病」,看上去只想戰決,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拉鋸戰。
但趙非凡還是晚了一步。買主畢竟已經拿到鑰匙三天了,已經進屋進行初步清理,丟掉了一些家具和零零碎碎。簽訂完買房協議當晚,趙非凡又在垃圾箱翻找了好一會兒,搶救出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但終究,有些前兩天扔的東西註定是找不回來了。
這個周末,我幫趙非凡把他的東西從酒店公寓裡搬出來,帶回家裡去歸置。兩個大男人爬上爬下,扔掉的杯盞重擦洗,摘掉的畫重上牆,歪七扭八的書架和沙發,又費九牛二虎之力,推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去。
他竭力要把房子復原成雲想濤還在時的樣子,藉以承載他的歉意與緬懷。
他端詳著重掛上牆的畫,貌似無意地說,蘇老師,還記得你曾經問過我,如果劉言那檔事繼續發酵下去的花,我會不會把這事兒披露出來。
我說,嗯?
「其實,還是會的。」他手扶在畫框上,裝模作樣地左左右右地調著,「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在給自己一個期限,等什麼時候忍不下去了,就把這事捅出去。當我發現自己存了這個念頭時。我就知道,我倆終會有這麼一天,或早或晚。」
我沒說話,有些話,我拿不準該不該跟趙非凡說。那天在機場,我最後一次問雲想濤,我說截圖那檔事,你就打算一直瞞著非凡老師?瞞一輩子?——我覺得不至於吧,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見過撕得你死我活的怨偶,也見過分開時哭得肝腸寸斷的情侶,走到最後,無一不是把話都說開,心結都放下,跟對方也跟過去的自己握手言和的。像雲想濤擰巴成這樣的,著實不多見。
雲想濤笑得神秘,他說不用啦,蘇老師,請你一定、一定不要跟非凡提起這件事。
他說我跟非凡好了這麼久,他是這個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我覺得有朝一日,他是能想明白的。倘若他一直都想不明白……
他頓了頓,就當我倆這段感情敗得徹底,那就更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趙非凡沒注意到我的沉默,還兀自在那兒絮叨。「其實直到現在,我也不認為想濤是個壞人,我也不覺得自己是個多高尚的聖人。想濤為了我可以拋下一切,但我卻不能為他做到同等地步。我明明知道他的不容易和不得已,但還是逼著他做選擇,因為有些情義我沒法放棄,有些事我沒法妥協。」
他說蘇老師你不知道,想濤他是個多謹慎、多聰明的人,我不相信他會讓隨便什麼人就鑽了空子截了圖,我思來想去,這個事,除了他自己爆出來之外,其他可能性幾乎為零。就沖這點,合該是我欠他的。
他說,一碼歸一碼,他傷害劉言的,已經都還了,道義欠奉的,他的代價也夠足了,獨獨我辜負他的那份,想來他是對我失望透頂,連彌補的機會都不願給我。
我想了一會兒,問他,「那天你讓我在機場攔住他,說還有話跟他說。你要跟他說什麼?」
趙非凡這會兒卻羞赧起來,過了好一陣才低聲道:「我本想說,你去哪我就去哪,這一次,換我跟你走。」
——不要辛苦打拼的事業、名氣;不要垂手可得的升職、加薪。多年前雲想濤為他的付出,他願統統在自己身上再過一遍,哪怕人到中年從頭再來比多年前還要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