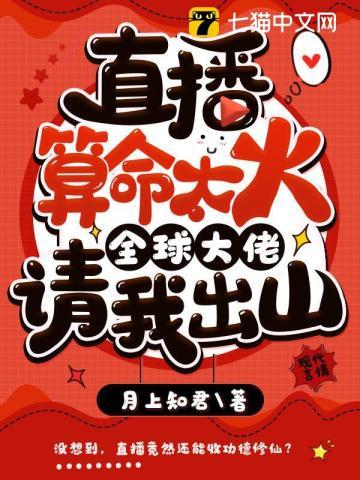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长命万岁是什么意思 > 第77节(第2页)
第77节(第2页)
天子这次突然对三省官吏动手,就是谁都预料不到的。
家中相处了十几年的兄弟姊妹,但是都免不了要各自走各自的路,眼睁睁看着高楼坍塌,她又怎么可能逍遥自在。
见女君在沉思,以为是听进去了,玉藻一鼓作气:“女君千万不要因为谢家而冷落了家主,那就是‘得不酬失,功不半劳’了,就算怎么样,女君也要想想大娘子。”
虽然玉藻遇到关于女子的事情,总是管不住自己的脾气,但是真要到女子心神被扰的时候,她脑子又能清清楚楚的。
谢宝因抬头望向屋檐下面那只从谢家来的鹦鹉,自己怎么会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也未必就是谢贤的尚书仆射被动了,只是想到谢氏将来的结局,心里就难免会生几分惋叹。
“这里好冷。”
她终是说笑道。
听到这句话,玉藻安心下来:“家主在居室,女君快回去。”
谢宝因吐口出气,缓步走回居室。
室内,男子散着还带湿意的墨发,踞坐在几案北面的坐席上,重新看起了那卷论道的《坐忘论》。
她脱下披在身上的鹤氅裘,拿去东壁的横杆处归置好后,去到几案旁的东面跽坐,然后拾起交刀,干脆利落的吧烧完的灯芯顶端剪去,火苗闪了下,很快就燃得越来越亮。
眼前忽亮,林业绥抬眼,瞧着在安静忙碌的女子,主动开口说道:“郑彧调任为中书省长官,我到尚书省去填补他的空缺。”
谢宝因放下交刀,臀骨慢慢往后坐下去,并拢的双腿被压着,她重新拿起前面的竹简,听到男子说的话,直接便应:“陛下竟然让郑彧担任了中书侍郎?”
她倒是不奇怪皇帝能够这么顺心的就改变三省长官的任用,毕竟三族中的主心骨郁夷王氏已经罢手不管,她父亲谢贤又是司徒,郑彧心里肯定有所不满,现在他眼前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过,而当另外两个都同意了,父亲要是聪明就不会反对。
只是中书省是三省中权力最高的,为事实上的第一宰相,中书令虽然是中书省长官,却不过是个空壳子,仅仅只在太。祖朝和高祖朝任用过,其余时候都不常设,都以中书侍郎为长官。
自从前年中书侍郎病故,天子也不再置,政务都由几位中书舍人共同商议。
林业绥看不进去竹简上面的字,干脆不再看,视线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女子,开口答她:“任为中书令。”
不管是中书令还是中书侍郎,在这三年间,中书省都已经早被天子实际掌握,否则怎么还敢让郑彧去。
谢宝因刚把竹简摊开,试探问道:“陛下是不是已经动了那种心思。”
林业绥伸手揽住坐在自己右手边的女子,手掌极其自然的落在腰上,然后抱人来怀中,听到这样的问话,肃然起来:“三大王和七大王都入了宫。”
谢宝因乖乖待在男子怀中,长睫垂下,竟然没有太子。
三省官员突然调动,还齐诏两位大王。
要是天子真的崩逝,又改了储君人选。。。三省长官一直都是被托孤的人选,新帝如果没有正当理由,难以下手,自然就会用尽手段解决。
被先帝亲点进入三省的男子岂不是入了虎口。
她想着想着,便失了神,手往竹简那边去摸的时候,忽然嘶了一声,食指被交刀扎出了血,不知是急的,还是痛的,往后抬头看向男子的时候,眸中波光粼粼,但是又说不出一句话来。
自从长生殿出来,心情便一直沉郁着的林业绥往下垂着眼帘,看到怀中女子这副样子,反而变得轻松起来,抬手去碰她的下眼睑,泪水即刻沾染上来。
“东宫已经快有子嗣诞下,太子也收敛了脾气。”
他安抚道,“而且还有我在,朝堂也不是郑家独大,天子想要轻易改储君人选,也非易事。”
谢宝因抹去指腹上的血滴,轻轻点头,转瞬笑开:“我只是疼的。”
林业绥笑然,收回手。
谢宝因本来还想要说什么,但是发觉箕踞着的男子又重新在看案上的竹简,她也不再开口,看他那么认真,不知道要看多久,自己总不能一直这么窝在他胸膛里,所以挣扎着想要从他怀里离开,但是却被横在腰上的手臂又给重新带回。
林业绥闷着笑了声:“陪我看看书,你昨夜不是喜欢看这卷。”
谢宝因也就不再动,安心待着,

![媳妇她成精了[八零]](/img/3827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