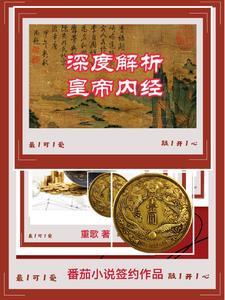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死对头穿成我的猫草履免费阅 > 第5章(第3页)
第5章(第3页)
“九年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没疯到底,”
他手握着烟灰缸弧度圆润的边沿,把烟灰缸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因为抽烟嗓音沙哑,“我现在都敢幻想出你这么久了,席必思。”
幻觉维持的时间一般不长,经常变换,很多是毫无逻辑的、诡异的线面结合,很少是他认识的东西,或者人。
大多数时间里,谢松亭思绪都是放空的,情绪断线会有,但只有一会儿。只要意识到自己病,他就会提醒自己及时收敛,幻觉也会随之不见。
席必思的幻象是个特例。
在今天之前,它只是偶尔出现,几年见不到一次。
可现在……只是和席必思的事有关,他就会看到他的幻象这么久。等猫住进来,他岂不是得天天对着席必思的脸?
烟灰缸沾了水,湿滑。
谢松亭抖着手,努力了几次才把它放在洗手台上,不想再往下想了。
他在逼仄狭窄的卫生间里蹲下来,双手抱紧自己的头,低声喃喃。
“求你……”
他的手臂和乌黑凌乱的头缠在一起,盖着他,覆住他,变成他隔绝外界的、纠结的障壁。
一侧脸,谢松亭蹭到自己满是疤痕的左胳膊。
那上面都是陈年旧伤,长长数条,深浅不一,肉色的,相比皮肤更凸起,周围点缀着短短的小疤。
小疤无一例外都很深。
幻象在他身旁蹲下,低头欲吻。
谢松亭猛地撤开胳膊,猝然抬头:“滚!”
它总算散了。
它还好散了。
他醒来时刚过中午十二点。
谢松亭基本没睡,草草洗了把脸就接到短信提醒。
飞机马上落地。
他没带烟,坐上出租才现,想折返已经晚了,只能厌烦地动动手,让衣料摩擦昨晚的新伤,转移注意力。
司机问了好几遍去哪。
谢松亭回神,报出货运站的名字。
到了地方,先在大厅递交身份证和提货号,交提货费,再去货运站里找猫。
货运站占地面积很大,内里更是比谢松亭想的还要大得多。而猫咪在离入口最远的提货口。
谢松亭走到地方时一脑门子汗。
他常年不运动,走几步便气息不匀,现在只能脸色煞白地站在行李前面,把收据递给工作人员,等她把猫拿给自己。
冷汗从他额头蜿蜒着落到眉弓,要掉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