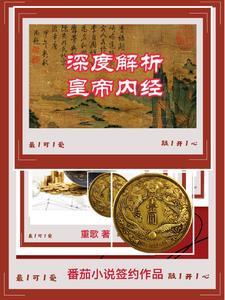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所以把主角都攻略了 > 第37章(第2页)
第37章(第2页)
“师父在棺里放了什么?”
冼清尘笑道:“你目力真好。”
楚回舟觉得不是他目力好,只是他的视线向来围着师父转,这才能捕捉到师父一个掩人耳目的小动作。
“我私心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和方姑娘在一起,仅此而已。”
他放得十分隐蔽,方家人合棺时不会注意到,她脚边新添一个拳头大小的小瓷瓶,里面是挚爱她的狐貍的骨灰。若是奈何桥上能相遇,不要再做一人一狐,哪怕是做两棵相伴而生的小树,彼此听得见树叶的沙沙摇动,共享一片日光和雨露,那也很好。
冼清尘先上了马车,楚回舟在上去前,听见有前来吊唁的僧人说话,说鸣雷寺一位师父死了,已经一把火烧了,愿他涅槃登极乐。
他一脚跨上马车,与冼清尘并肩坐下,又眼尖地看见师父耳垂上的那颗小痣,小痣上溅了一点红红的东西。
楚回舟鬼使神差地抬手去擦,意识到那是一点干涸的血迹,和佛堂地板上的红色蜡油一样,粘在冼清尘耳垂上。
冼清尘累的没有躲,抬起眼皮看了看,眉心一跳,却自然接话道:“怎么溅到这里了,我都没有发现。”
“回舟,借我靠一下吧。”
他在楚回舟左肩上靠下来。
“师父?”
楚回舟紧张起来,不是为了这个动作,更多的是为了这个称呼,很少听见的一声“回舟”
。
冼清尘没有回应,安心闭上了眼睛。
他想狐貍有一句话说得对,既然快乐,就应该珍惜。与楚回舟在一起,如果不去想往后的事,真是一件放松又快乐的事情,冼清尘决定要对楚回舟再好一点,要做师父就好好做师父吧,不要再做明明有钱还把楚回舟骗去打工的蠢事了。
一格又一格的光落在他眼皮上,叫他想起昨夜跳动的烛光,以及抱秋子在他扇刃下平静的目光。
他本来还奇怪,为何抱秋子进来后,没过一会儿就屏退了其余人。
“清尘,我知道是你。”
他说。
冼清尘在惊讶中睁开眼睛,面无表情地坐了起来。
抱秋子看上去是个六旬老人了,银发不太齐整,潦草地扎着。他抖开陈婆的信件,仔仔细细地读起来,道:“多谢你带信给我,小陈是我最后一个徒弟,老夫做了一百六十二年医者,所有的医术早已倾囊相授,也算可以瞑目了。”
冼清尘按下心底隐隐的烦躁:“你知道我是来杀你的?”
“我总知道会有这一天的,自从冼清尘这个名字出现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他看完信,心平气和地折好,烧掉了纸张,“小陈还是这性格,真是怀念以前的日子。”
冼清尘一点也不关心陈婆在信件里写了什么东西:“我恨你。”
他只是直白地描述出自己此刻的直觉。
抱秋子很平静:“你没错,当年的事,是我们让冼家遭了灾祸,清尘,我们这群老人太害怕变数了,错不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