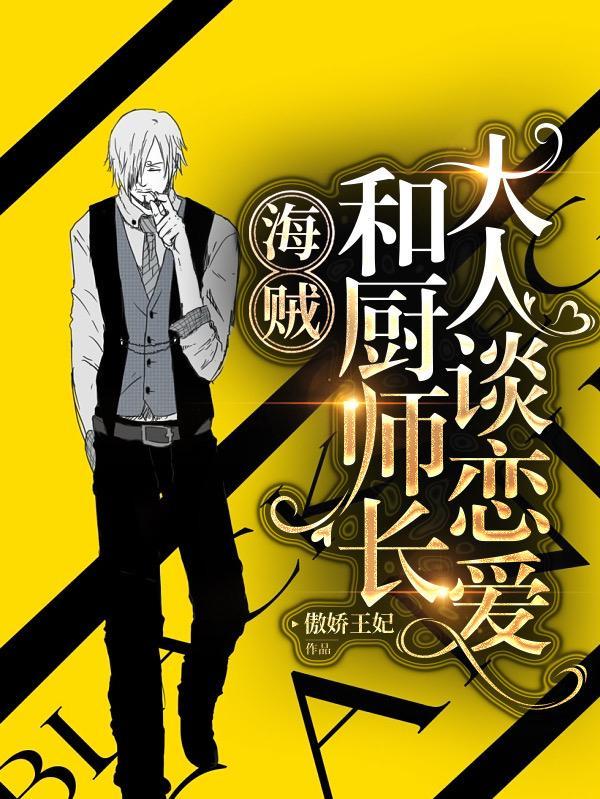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情陷夜中环[粤语 > 第197頁(第1页)
第197頁(第1页)
念念最後那句話,說的那麼無可奈何,說的那麼絕望。那一瞬,仿佛對她所有的恨全都隨著她縱身跳下的一瞬間,灰飛煙滅,破了,碎了。
腦中,一片空白,像是斷了片。
沈仲凌和林霖下去的時候發現念念沒有當場死亡,還有一口懸浮的氣遊走在鼻腔里。
警車和救護車相繼趕來,江嶼風隨車到了醫院。經過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搶救之後,醫生從裡面走出來,問了句,「家屬在哪?」
江嶼風站了出來,點頭示意,一開口便是一句,「我是。她,生,還是死?」
「沒死,只不過她的後半輩子都要在床上度過了。大小便都不能自主。脊椎斷裂太嚴重了。」語落,醫生深嘆了口氣和江嶼風擦身而過。
江嶼風一聽,腦中轟得一聲。
終身癱瘓,這是報應嗎?如果是,也太殘忍了些。
一步錯,滿盤輸。
這場棋局中,她也是受害者,可她卻沒有用正確的方式活下去。結局,早在她做出選擇的一刻就註定了嗎?
修長的腿邁到門邊,頓了好久,他才有勇氣推門而入。
病榻之上,她嬌弱的就好像夜晚的風一樣,握不住,碰不得。
江嶼風走到病床前,筆直地站著,不知不覺就紅了眼。自以為瀟灑的縱身一跳竟然落得個生不如死的下場。
當他真的受到報應的一瞬,江嶼風才發現,這一切有多慘烈。倒不如一槍結果了他,還不至於在往後的日子只能承受源源不斷地痛苦。
消毒水的氣味好濃稠,不但刺鼻,還刺眼睛。早沒理由為這個女人落一滴淚,可當下他的眼淚卻不由自主地應景而落。
門,嘎吱一聲開了。
江嶼風把眼淚往回收了收,平復著自己的心情。
身後,響起沈仲凌的嗓音,「江嶼風,出來下。」
他轉身,淡淡回了句,「好。」
醫院的走廊上,急診室的這一片向來都沒有安靜的時刻。不斷有推床與他們擦身而過,每個人的腳步都是匆匆的。
沈仲凌看了眼身邊剛被送來的病患,家屬正在哭鬧,差點跪下來求醫生挽救一條幾乎不可能救活的生命。這世界上求生的人那麼多,可有人選擇了求死。
低嘆了口氣,輕輕拍了拍江嶼風的肩膀,「我知道現在不該說這件事,可是……」
江嶼風似乎聞到了一股子他難以承受的氣味,眸底深處的恐懼不言而喻,壓低聲線回了句,「你想說什麼就直說。」
「柏嘉榮自了。」
江嶼風一聽,一把抓住了沈仲凌的外套,倏然瞪大雙眼,「什麼?你怎麼不早說?」
沈仲凌皺著眉,深刻理解江嶼風的心情,「場面太混亂,我是沒有機會說。」
心臟仿佛被電擊了一般,瞬間麻木得不行,出口的聲音都在發抖,「他現在人在哪?」
「在警局,明天一早就送到看守所。」
他艱難道,「簡年知道嗎?」
沈仲凌搖頭,「還不知道。」
腳步,跌撞了好幾下,江嶼風鬆開手,緊緊捂住了心臟,「暫時不要告訴他。」
沈仲凌點頭,「我明白……」
車子一路行駛,江嶼風緊緊咬著自己的嘴唇,心中的痛感洶湧而至。
他細細猜想念念去找柏嘉榮的原因。念念到底說了什麼,才會讓柏嘉榮這麼快走進警局俯認罪?
油門拉得很高,短短几分鐘,他便載著沈仲凌回到警局。他們趕到的時候,林霖已經給幾個被拐女孩做完了筆錄。見到江嶼風進門,他一下便站了起來。
濃重的陰霾逸在江嶼風的眉梢,他的雙眼如被夜色渲染,沒有一絲清明。
林霖什麼也沒說,對他使了個眼色,帶著江嶼風來到關押柏嘉榮的屋子。
江嶼風進門,林霖和沈仲凌都撤了出來,整個空間只剩下著經歷了無數滄桑和炎涼的兩個親兄弟。
江嶼風走近,哽咽著,「你還是這麼做了?」
柏嘉榮慵懶地坐在鐵欄內,笑了笑,「不用為我難過。我想了很久。這樣,是最好不過了。我可以下去陪我爸了。到地底下給他認錯,你說他會認我嗎?呵呵,應該不會認吧。」他的話無限悲涼,絞碎了江嶼風的心。
江嶼風伸手一把抓住了兩根鐵棍,顫聲道,「明明可以重來的。」
他搖頭,有些哭笑不得,「人生怎麼可能重來?真的不能!不要告訴簡年,好好照顧他。」
兩人沒說上幾句話,從外面進來了好幾個人,其中還包括老岳的女兒。按照慣例,柏嘉榮認罪之後,警局有必要通知受害者的家屬,只是他們來得太快。江嶼風和柏嘉榮連多聊上幾句的機會都沒有。
墓園警衛員的老婆手裡拿著框雞蛋,一看就是有備而來,猩紅著雙眼,毫不猶豫地對準柏嘉榮丟了過去,一邊哭,一邊切齒道,「你這個殺人兇手,害死我老公。」
老岳的女兒也被身旁的大嬸帶起來,眼淚唰地一下就如噴泉,「殺人兇手,還我爸爸。」語落,她從大嬸框裡奪過一個雞蛋也狠狠砸了過去。
再然後,所有人都邊哭邊扔。
柏嘉榮自嘲地笑著,蛋清和蛋黃將他的黑髮黏連在一塊,蛋殼被髮絲勾住,幾個碎片垂到了眉心。
縱橫在金三角的一方霸主,生平可是第一次被人扔雞蛋。他擼了把臉,低低道,「該砸!是該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