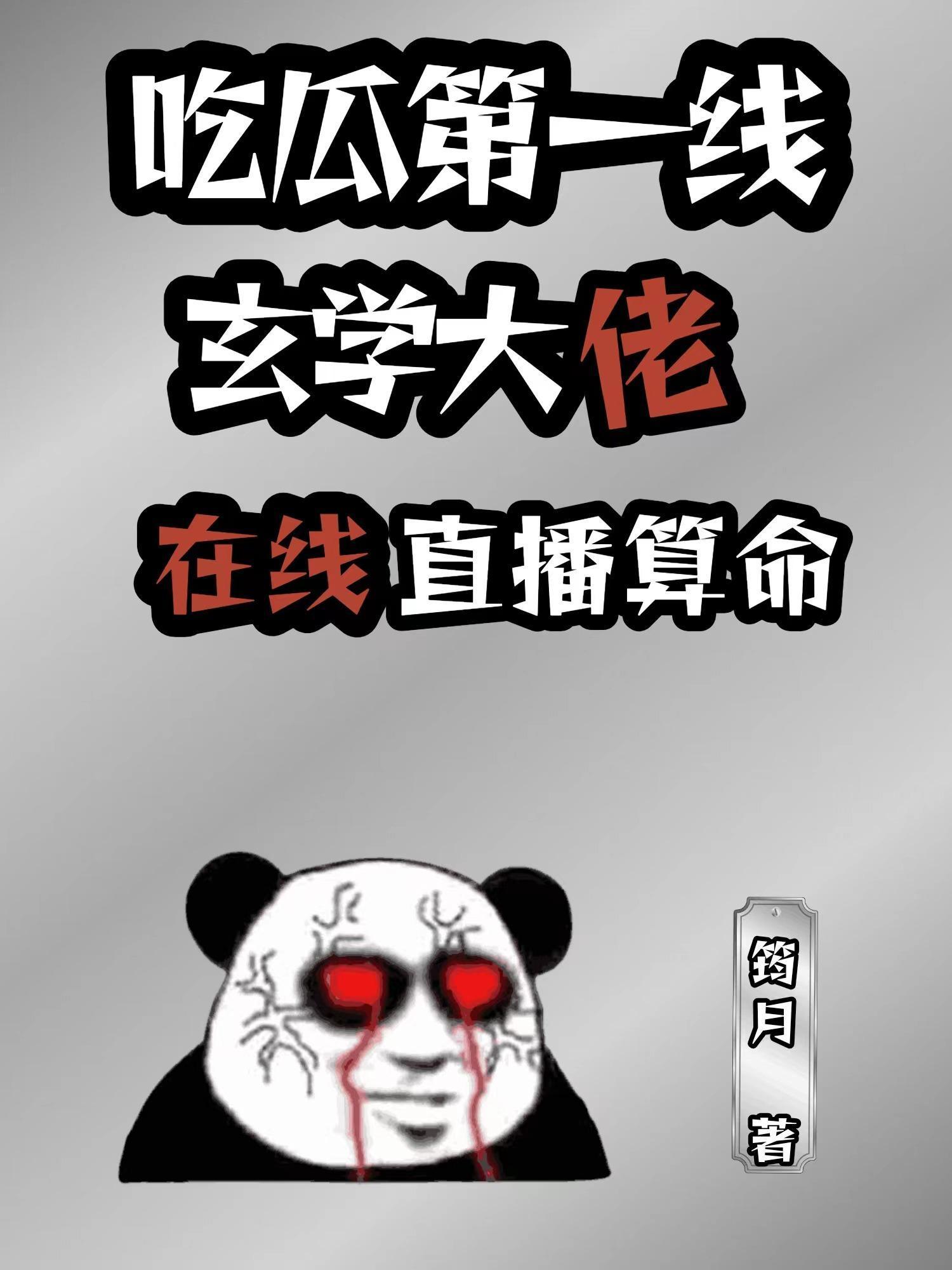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没得救作者不临月 > 第85章(第2页)
第85章(第2页)
刚搬来那会儿,等霍妍上了学,宋建兰就天天以泪洗面。老太太不认识母女俩,只听说是因故借住的远亲,瞧着也确实眼熟、面善。
她颤颤巍巍地拿了个小橘子剥好,递给了宋建兰,说:“别哭啦,闺女,吃一个吧!”
“……谢谢。”
宋建兰接过,吃着吃着眼泪又流下来,把老太太弄得不知所措。
“对不起。”
她抱歉说,“是橘子太酸了。”
晚上,宋建兰把沈庭御叫到房间里,让他可以坐得再近一些,不再哭了,慈眉善目的。
沈庭御立时便看出来,霍也身上那股与他凌厉又俊美的长相并不相符的气质,那股刻在骨子里的矛盾的温柔到底是像了谁。
“好孩子,乖,到妈妈这儿来。”
宋建兰像是认识了他很久似的,轻轻地拉着沈庭御的手。
沈庭御心中触动,顺势在身前蹲下,安静乖巧地仰起脸来看向她,漂亮眼眸一错不眨。
宋建兰怜爱地捏了捏他的耳垂,怕惊醒了不知谁那样,轻声说:“我家小七,你不要看他好像随心所欲,什么也不放在心上,其实是个很拧巴的人,还有点儿胆小,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胆小,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坚不可摧。”
“他说没事,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在这一方面他很不诚实,经常边笑边撒谎。”
“临走前,那天他也像现在这样,趴在我的膝盖上认真告诉我,——因为喜欢你,所以跟你在一起的很多时候,他都感到很幸福。”
沈庭御听到这些戳心的话,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忐忑地问:“真的吗?”
“不觉得我很任性很难伺候,或者跟我相处很累吗?这样的我,原来他也愿意喜欢吗?”
“喜欢的呀。”
宋建兰微微笑着,柔和眸光像夜里指引迷途的灯火,“小七胆小,料是没有说出口的,他不敢说,我做妈妈的来替他说。”
沈庭御仔细听着,生怕错过一个字,眼里黯淡很久的光,一点点地亮了起来。
宋建兰说:“我昨晚梦到小七,他拜托我一定叫你不要自责,不要担心,替他完成没能完成的约定,实现他没能实现的梦想,好吗?”
沈庭御心头一震。
良久,他才扬起眸来:“我明白了。”
沈庭御颓丧多日,终于振作起来,而那时距离高考还剩下三十多天。最后一张拟志愿表发下来,他不再重复单调的写那几个字,第一志愿改成了国内政大,其他空行的一律没填。
他把这些天落下的学业捡起,将所有精力投入进去,确保分数绝对稳定;他还是会私下悄悄地抽几根烟来缓解思念,好在那两个月的戒断攒足了分开的经验,不过就是生离死别。
关于身后的事情,沈庭御不去管,连他的名字都害怕听、害怕提,好像霍也真的只是去忙了,他们总有再次相见的那一天。
什么墓地,什么告别的仪式,通通都是不存在的,沈庭御从没去过,假装着从未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