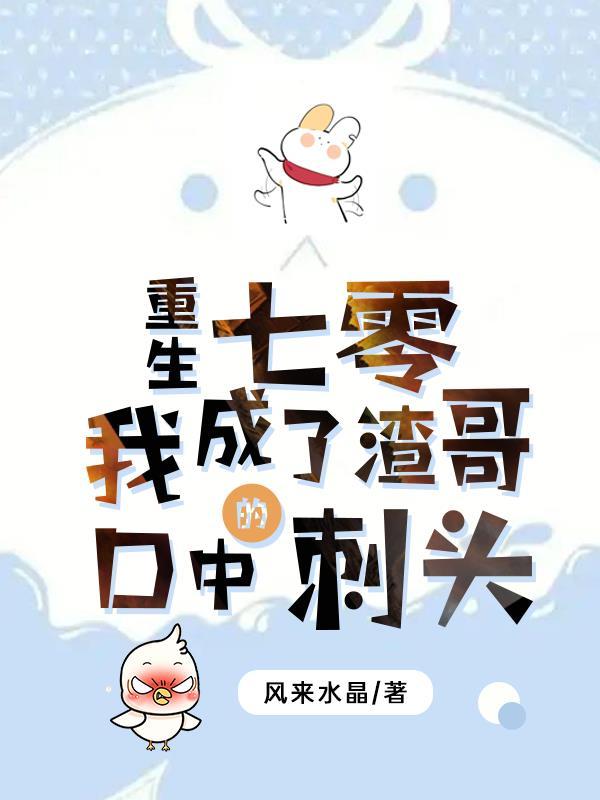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假死后夫君火葬场了免费阅读 > 第53章(第1页)
第53章(第1页)
但男子并不急着进来,而是一直保持着掀毡毯的姿势,待后面的女子进来后,他才猛地将毡毯放下。
为首的女子一袭黛紫袄裙,外披羊裘披风,双手、双耳、头顶皆有御寒之物,一半脸清丽异常,另一半脸被一道疤硬生生毁掉,正款步向里走来。
陌生又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陆怀砚平静的心湖有了些许波动。
他失神地望着面前这名女子,一眼认出这便是两年前葬身于火海、他曾经的妻子——云梨。
店内最后进来的那女子被毡毯拍了个满脸,气得大吼一声,“关野!”
陆怀砚也因为这声吼叫回过神,云梨还活着,虽在意料之内,但更多的是意外,没想到再重逢时竟会是在她所开的酒肆里。
最让他意外的还是她那毁去一半的脸。
猜到她可能是假死离开上京后,陆怀也没逼迫凝霜说出真相,想着她既选择以假死离开,想必心中不愿再与他有过多纠缠,他便顺势而为成全她。
只是在看到她脸上的那道刺目疤痕后,他的心到底不能平静,心生愧疚。
眼看云梨越走越近,一旁的言聪眼睛都瞪直了,疯狂示意陆怀砚,陆怀砚却像是没看见般,淡睨了他一眼。
陆怀砚以为云梨会认出他,但她视线并未在他身上停留分毫,而是对一旁的曹知县恭敬行了一礼,声音低柔温婉,“知县大人安好。”
曹知县笑笑,指指身旁的陆怀砚,“眼里可不能只看见我一名知县啊,这是枫河县新上任知县陆知县。”
云梨以同样的姿势向陆怀砚行过一礼,“民女见过陆知县陆大人。”
陆怀砚见她低垂着头,敛着睫,教人看不清神色,与他说话是满是疏离之意,她整个人说话时的语气、行礼时的动作大方又得体,与印象中的她差别实在太大。
陆怀砚起身,不知是动作太大、还是狐裘的过,桌上的酒杯被狐裘扫落地面,清脆的响声响起,杯子里的酒也倾洒出来。
云梨心中不愉,这酒杯是她专门托人描了喜欢的花样订做而成,还没用多久,酒杯成双成对共八十八只,单取一个“合”
意。
陆怀砚只垂眸淡淡扫过地上的杯子,“抱歉,这酒杯我会赔付双倍银子。”
说完,他声音温煦道,“阿梨……”
云梨攥紧的掌心豁然松开,这是她云梨的酒肆,当由她做主,她不用再像从前在陆府那般谨小慎微、卑躬屈膝。
后面的话还未说出口,云梨便不由分说地打断,眼神温柔而坚定地直视着他,“陆知县,你认错人了,也叫错了,我叫云梨,不叫什么阿梨。”
“二位慢用,云梨先行告退。”
说完向两人微微欠了欠身,转身离去。
云梨一走,气氛肉眼可见地变冷不少。
曹知县以为陆怀砚是因为云梨方才的举动而动怒,忙劝他,“还望陆知县别往心里去,这姑娘平日里不这样,想必今日是有什么心事,她没什么坏心思。”
陆怀砚掀起狐裘重新落座,一双桃花冷幽深邃,“无事,敢问一句,曹知县为何会帮她说话!”
陆怀砚用的是帮而不是替,就意味着他断定曹知县所言并非是假意客套。
曹知县擦了擦额上不存在的汗,一句话就让这人看出了自己的心思,可怕,太可怕了。
曹知县喝了一口堂倌重新斟好的酒,舒服地叹上一口气。
“想必陆知县也知道,像关氏这样的商铺,是税收大头,而且每岁还会捐出一笔善款用来加固河堤、修缮道路这些,咱们当官的,多少都要给他些面子吧况且,关野那小子只是让我在他外出跑船的时候,能够帮忙照拂云姑娘和离忧居一二。”
陆怀砚看看他手中的酒杯一眼,抿唇道,“曹知县不必紧张,我并未生气,只是方才看见云姑娘,想起一个故人罢了。”
再见时,她身边多了一个能够照顾她的人,她似乎也变得更好、更耀眼,没再沉湎于过去的伤痛中,这没什么不好。
陆怀砚提起故人,曹知县自然不会将云梨和陆怀砚和离的妻子联系在一起,毕竟以陆怀砚的眼光和身份,肯定不能娶一名容颜有损的女子。
曹知县忙不迭点头,“理解,故人之姿而已。”
陆怀砚凝着曹知县手里的酒杯已有半晌,冷不丁地问,“这酒也是云姑娘酿的!”
陆怀砚不好直接开口讨酒喝,只好以这种方式开口。
方才不觉这酒有何特别之处,如今再闻,竟觉得清香扑鼻。
曹知县替陆怀砚斟上一杯,“那陆知县今日就尝尝这梨花酒,看看味道如何!”
陆怀砚轻握酒杯,垂眸沉思片刻后低喃出声,“梨花酒么!”
而后喉咙一滚,酒入腹中,先是有股难以言喻的苦涩之感齐涌而上,渐渐地就能品出一丝甜意来,最后竟然甘中又带有淡淡的苦,后劲太大。
像是经历万般苦难,而后终是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有股辽游于广阔山水间、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甘中带苦实则无甘唯有苦。
见他喝下,曹知县一脸期待地问,“如何陆知县。”
陆怀砚转着空酒杯,“确是好酒。”
曹知县,“那是,这梨花酒先苦后甜,喝的就是那股甜。”
陆怀砚笑而不语。
刚喝完一杯酒,陆怀砚脸上就浅红一片,笑的那一刹那,肃沉尽散,多了几分风流。
*
云梨拿出账簿盘账,吕兰英走过来,朝陆怀砚那边看了一眼,“那就是你掏心掏肺、死心塌地爱过的负心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