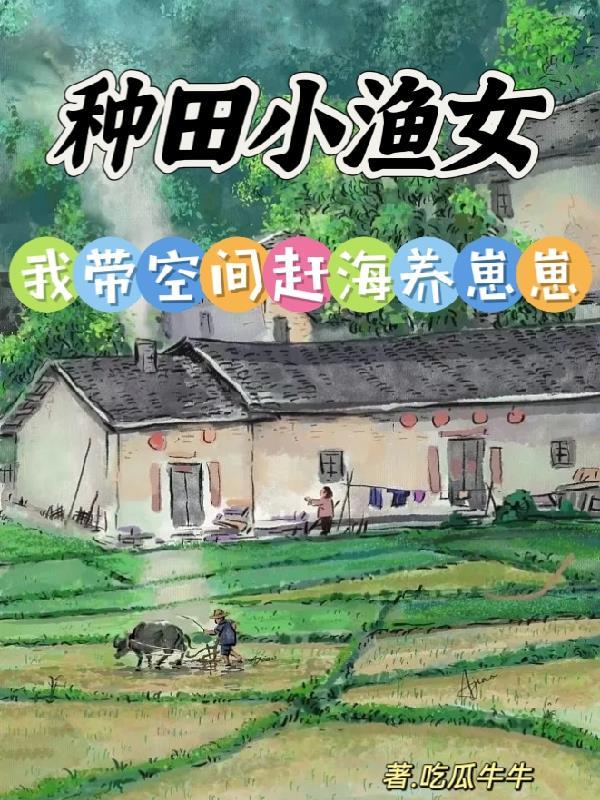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月半小夜曲左麟右李 > 第63章(第1页)
第63章(第1页)
李君等到红婶子把其他菜炒好了,才去拿碗筷盛饭坐下来吃。
这新开的鹅馆,用的是地道的乡里土鹅,没沾饲料味又天开地阔到处跑的鹅,家常做法都香,更何况是这样用大五花肉拌着一起炒。鹅肉味道确实可以,李君试了下,辣味也不算太过火,她不吃甜,但能吃辣的。
红婶子沉默,没像平常那样话家常。洪秀琪反倒主动说了句:“李君,谢谢你带菜啊!”
吴拥军擡头看她一眼,心里更加拿定了主意——他们正经的同事都没说话,她一个蹭饭的倒是主动了,尬不自知呀!
身为站长,罗常富一向来得比较早。他家负担重,又住在路边,没有买摩托车,要麽就在路边顺手拦个便车,要麽骑着个自行车来去。
他六点不到就来了,李君跟他说了句,他把保险箱开了,让李君把钱也存了进去。
夜里没有多的添菜,除开特意留的一碗鹅肉,那一大盆也没吃得完。
这一餐,红婶子没好意思喊女儿来,只在吃完后问罗常富:“站长,你没来,牌都打不成器,今夜里打不打?”
罗常富不在,另外三个值班的,一个黄波想打,袋子里总没几十块钱。一个李君,对打牌不情不愿的。
“可以啊,你快点做完事。”
红婶子没喊女儿来洗碗,自己飞快地收拾,然后讲一句:“我回去拿点零钱。”
等她再来,身后又跟着一个洪秀琪,这次没放肆喷香水了,穿着一条碎花裙,接地气了些。
黄波吃完饭就回家休假去了,吴拥军对洪秀琪已经没得什麽想法,没再油嘴滑舌,喊打牌就坐下来规规矩矩打牌。
罗常富喊李君玩,他配合坐下来,只是不声不响。
今天这场牌,格外安静。
红婶子从桌上拿了张十块钱的,递给身边挨着看牌的女儿,说:“你每日子在这里蹭饭吃,去买点东西回报一下咯。”
这是在家就商量好的,洪秀琪缓慢起身,年轻女孩,身量苗条,处在最好的年纪,动起来娉婷袅娜。就算吴拥军说服自己死了心,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李君依然木头股一样,只盯着手里的牌。
洪秀琪走了没几分钟,又拎着一袋子东西回来,贴心地找出个塑料盘子把瓜子倒出来,又帮着撕槟榔壳子。
她把撕开的槟榔往李君这头递,想喂到嘴边。李君早早地把手擡起来拦住,硬邦邦地说:“我不吃,谢了。”
最难消受美人恩。吴拥军脑子里冒出这一句,忍不住嗤嗤偷着乐。
李君看他一眼,罗常富拿丢出来的牌敲敲桌子,笑着问他:“什麽好事?说出来让大家一起乐呵。”
吴拥军咬住嘴,憋住笑了才说:“一天连着有好东西吃,想起来都幸福咧。”
“你这……啊呀,打牌打牌。”
打了几把,洪秀琪又起身给大家倒茶。
罗常富习惯性地夸了两句,顺嘴问起:“红嫂,这样懂事的妹子,你要好点选个郎谷子啊。我屋里侄子,嫡嫡亲亲的,二十五岁,中专毕业,在中心小学当老师,介绍给你屋里妹子,要得不?”
上次罗常富没提,主要是红婶子重点在不干农活上。罗常富回去后,随口跟堂客说了一句,他堂客反应快些,当即就回道:“你侄子吃国家粮(沿用旧说法,指有工作),又不要到田里去刨,怎麽不合适呢?他爷娘的田土,又不会要他们回去耕。你帮着问下子,要不然你侄子一直不找对象,连带我们屋里的以后也不好说。”
他这当老师的侄子要是今天之前提,红婶子保证心动,但中午开了眼界的娘女两个,都看不上只拿几百块钱工资的人了。
所以红婶子丢出一张a,状似吐槽地说:“啊呀,莫讲起,烦躁死哩。细伢子大了,哪里肯听我滴咯。她心里有喜欢的人了,死活只肯嫁那一个,我有麽子办法。只能辜负你的好意啊!”
洪秀琪就一副被说中心事的窘迫模样,擡头看了一眼李君,再娇羞地低下头“掩饰”
。
这下,在座的哪还有不明白的。罗常富有点尴尬,吴拥军只觉得好笑。人家李君清清楚楚说了“怕堂客”
,“快了”
,“吃喜酒”
,这俩位,还搞这一出。
李君淡定地出牌,因为罗常富一直看着他,他干脆说:“站长,你不是要帮我做媒吧?我有堂客了。”
他这话刚落,就听着马路对面小卖部那婶子大嗓门喊:“李君,李君,栏杆站李君,接电话咧。”
本来必胜的牌,李君一把扔了,飞快地弹跳起来,一阵风似的沖出去,只丢下一句:“你们先打,等下我回来数(给)钱。”
大家没动,嗑着瓜子等他回来。
他这一去,就是十几分钟,大家还起身上厕所走动了一下。他满面笑容回来了,手里拿着几包麻辣香干和牛肉。
一向不爱说话的人,一坐下来,笑得热情,招呼大家吃东西,出牌都有声了。
罗常富惦记他出去前那句话呢,撕开一包麻辣,先问再吃:“你说有堂客是怎麽回事?”
李君调来才几个月,来之前站长肯定是要知道点底线的,家在哪,单身还是已婚。
李君乐呵呵地说:“快了快了。”
吴拥军龇着牙倒吸了口气,担忧地问:“刚才是她打的电话呀?”
李君含笑点头,然后又遗憾地说:“她不同意我给她买手机。”
要不然他就能随时找她说说话了。
罗常富倒是高兴,他自认是个叔辈,就爱看后生仔一个个顺利成家,“人家是心疼你赚钱不容易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