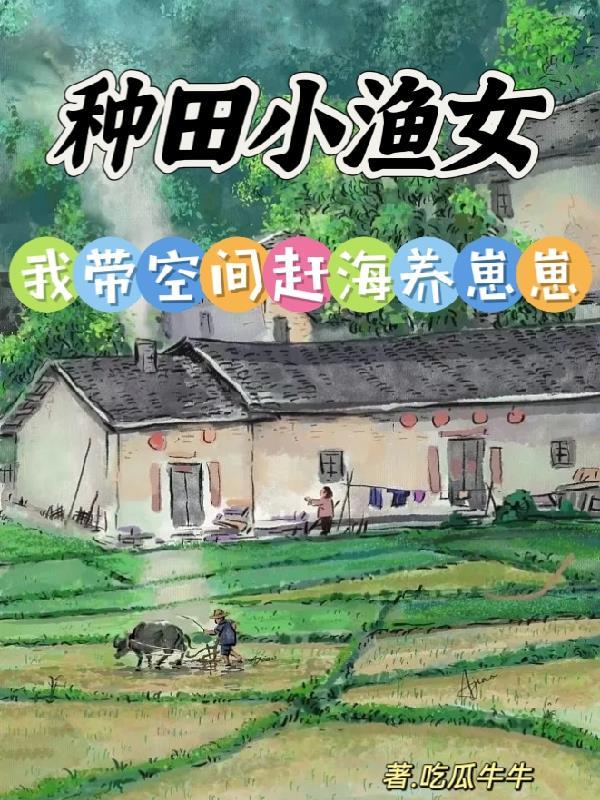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穿成了阴郁反派的白月光星光遥 > 第8章(第2页)
第8章(第2页)
江稚很惊讶,“这么久了你还记得?”
“没,就是突然想起来的。”
江予闭着眼,白炽灯迎面罩下来,浓卷的眼睫在嫩生生的脸上落下一小片阴影。“吱吱,如果你知道你身边的同学转学后也会遇到霸凌,你会怎么办?”
校园霸凌。
每一个具有基本同理心的正常人在学生时代最厌恶、最恐惧的四个字。
江予想到了庄敛。
他的心在动摇。
尤其是在今天晚上在那条巷子里见到他之后,江予的心很煎熬。
江予穿书前曾经直面过校园霸凌,被霸凌的对象是另一个人,那个人在高考前夕从教学楼楼顶跳下,刚好落在从楼下经过的江予面前。
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江予仍旧记得当时浑身发冷的状态,所以他做不到在明知道庄敛也会遭遇校园霸凌的情况下冷眼旁观。
他有些焦躁。
急迫想有个人来推一把他,把他从煎熬中拉出来。
“小鱼。”
江稚温柔地说,“你心里不是有答案了吗?”
他已经听出了弟弟语气中的焦虑,“我们的小鱼从小就见不得别的小朋友被欺负,一直都是小朋友心中的小太阳,这次怎么了,是发生了什么吗?”
江予静了静,没回答,而是问,“哥,未来是可以改变的吗?”
江稚说,“当然可以。”
江予舒了口气,“我知道了,吱吱。”
“……你小子有事叫哥没事叫吱吱,你没事吧?”
江稚不高兴道,“兄弟谈心时间到此结束,挂了,早点睡。”
“吱吱再见!”
江予笑嘻嘻地抢先一步挂了电话。
江稚都懒得理他。
另一头,秫香别馆,西区,庄家的别墅。
庄家的几个主人早就已经睡下,下人们经过书房的时候不经意朝内看一眼,主家新找回来的那个不讨人喜欢的少爷被动了家法,被打得半死不活丢在书房罚跪。
大动肝火的庄先生下了死命令,谁也不准给他送药。
没有人为他说话,唯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庄曜在庄先生上家法前就让下人带回了房间,没有吓着他。
庄敛面无表情地跪在地上,腿弯处还有脚印,那是他刚才跪慢了那个所谓的父亲踹的,与背上的伤比起来不值一提,交横错杂的红肿鞭痕被粗糙的布料磨得火辣辣的疼。
被打习惯了,这点痛就会在忍受疼痛的阈值之内,没有那么难以忍受。
庄敛眼角阴沉,盯着锃亮的地板,他忽然想起来在那个巷子口,那个人对他说,“你受伤了庄敛,去买点药擦擦吧。”
庄敛以前挨完打总是没钱买药,于是渐渐习惯了自愈,但今晚鬼迷心窍从那沓打|黑拳得到的钞票中抽出一张拐进药店买了一支药膏。那只药膏放在书包里,还没来得及拆封,就被当成垃圾和书包一起丢进了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