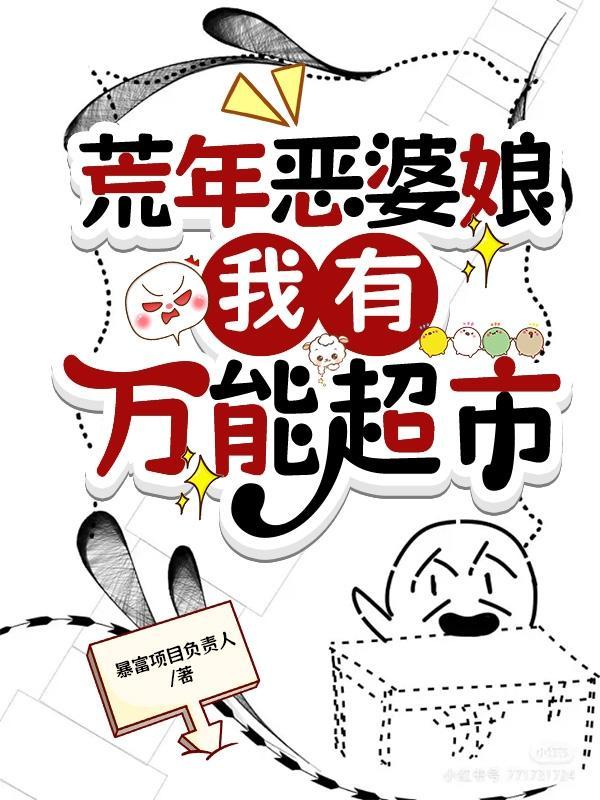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类比推理 > 第五十三章孩子十一(第1页)
第五十三章孩子十一(第1页)
“抱歉,我太累了,”
玛丽直勾勾地瞪着地板上的蛋液,安妮迷惑地看着她,然后蹲下身去试图将那些还未曾完全打碎的鸡蛋捞回到纸盒里——玛丽抓住了她“我太累了”
她重复道:“让它去,别管这个。”
“但是玛丽”
“我说不要弄了!”
骤然提高的声音不仅仅让安妮讶异地睁大了眼睛,就连玛丽也被自己吓了一跳:“好了,我说不要弄了。”
她放低声音,手指轻微地用力:“我会处理的,你现在回房间去。”
她顿了一顿,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语气和用词仍然在冷漠和暴躁之间徘徊。这样不对,玛丽对自己说,你和这个孩子已经相处了一年有余,她聪明,漂亮,听话懂事,身世凄惨引人同情,你了解她,熟悉她,你不该只因为一个只不过见过一两次面的新邻居以及新老师对你说了通奇奇怪怪的话就开始怀疑可怜的安妮?!——或许正如她之前所想的,安妮推荐给她的香料和菠菜汁不过是一种巧合。这个孩子固然早慧,但她的知识暂时还只能来源于网络和图书馆,她很有可能对这两种食物所能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它们的益处倒是一直被广为流传的)——毕竟在今天之前就连玛丽也不知道香料和菠菜会对孕妇有害——还未必真的有问题呢,不管怎么说,医生的忌食清单上也从未出现过它们的名字。
安妮看起来有点迷惑,但正如之前的每一次,她毫无异议地服从了。
玛丽看着安妮走出厨房,现在她不得不挺着一个坚硬硕大的肚子来拾掇地上的一片狼藉,这可真是不容易,鸡蛋是种奇怪的东西,它很难被弄干净,而且残余的部分很快就会散发出恶臭,招来苍蝇和蟑螂。她弄了足足半个小时,才勉强让厨房的地面踩上去不再有粘糊糊的感觉,等她把其他的东西放进冰箱、玻璃罐子或储物柜,一一安置妥当之后她发现自个儿的脊背和腰冰凉坚硬的就像块大理石塑像——她把拆下来的包装纸捏在手里,慢吞吞地回厨房的桌子旁,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平时,她会让安妮为自己揉揉肩膀,可是今天玛丽压根儿没想到这回事,她的脑子一团糊涂,需要好好整理一下她甚至想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打电话,她从未如此想他,她需要他在身边不过终究也只是想想,因为明天晚上肯特先生就能到家,并从这一天开始休他的四周带薪产假。
“快回来,”
她在心里说:“快回来。”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太累了,就算是坐在冰冷的厨房里,坚硬的椅子上,她的全身,从眼皮到手指仍然在不断地下坠她几乎就要睡着了,但一个细微但突兀地拉拽动作把她一下子从混沌中惊醒了过来,厨房昏黄的灯光下,安妮的琥珀色眼睛就像金子那样闪闪发光,细小的手指弯曲着插入玛丽的手心。玛丽本能地先是收拢手指,手心里凹凸不平的触感提醒了她,她举起手,才发现以为早就丢进垃圾桶的包装纸还被自己紧紧地握在手里。又过了几秒钟,她才进一步地明白过来——安妮是想帮助自己把垃圾丢掉。
“谢谢。”
她说。
安妮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个小任务,做完后她跑到水槽边洗了手,擦干,玛丽听到她的鞋子在地砖上咯咯的响,她走到玛丽身后去了,玛丽的肩窝上搭上了两只小手,小手带着潮意,有点凉。
玛丽的身体紧绷起来,她控制着自己不要逃开,这可太傻了,但她怎么也遏制不住那份莫名其妙的怀疑和忧虑不管那双小手怎么殷勤,她的身体一直没能放松下来,安妮似乎也已经觉察到了,她停了手,然后将两条白皙的手臂伸过玛丽的肩膀,孩子幼嫩的,光溜溜的,散发着牛奶味儿的面颊从后面贴近了玛丽的脖子,她说话时候散发出的热量掠过玛丽的鬓角。
“我们要给小猫什么?”
她问。
“毛线球。”
玛丽干巴巴地回答道。
“我们要给小狗什么?”
“肉骨头和散步。”
“我们要给小男孩什么?”
“弹弓和青蛙。”
“我们要给小女孩什么?”
“无数的吻和甜蜜的拥抱。”
安妮从椅子后面转了出来,她小心翼翼地侧着身体,以免压迫到玛丽的肚子,她在索求奖励——玛丽犹豫了一会,伸出手臂,抱住了她。
这是一个曾经很讨玛丽欢心的小游戏,性情方面更像个小男孩的多洛雷斯从来不会和她玩娃娃或者这种“酸溜溜”
(多洛雷斯语)的文字游戏,直到安妮出现在这个家里——养母女的头颅彼此轻轻摩挲着,玛丽闭上眼睛,她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和这个孩子彼此拥抱和亲吻的感觉,那就像是含着一块巨大的、温暖的,甜美的,永远不会融化的棉花糖。她想要再次找回这种感觉,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