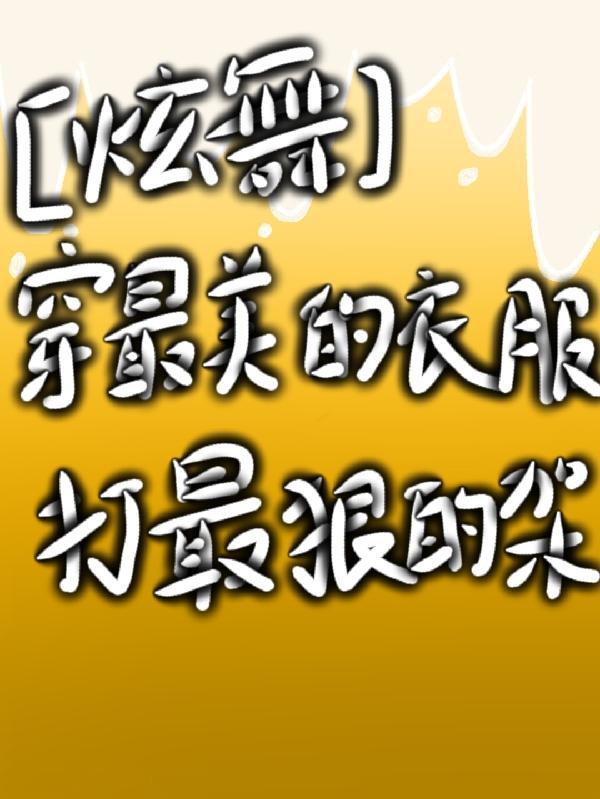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靖安2023年GDP > 第3章(第2页)
第3章(第2页)
“阿淑,殿下,公主?”
裴裕低头服软,“好阿淑,和你说正事,过几日便是清明雨汛,新安江上游的堤坝年久失修,居心叵测之徒大可在此处做文章。”
杨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人为毁堤淹田、强行改粮种桑,她匪夷所思地看向与她并肩而行的裴裕,眼神中写满了丧心病狂。
裴裕迎着杨淑质询的目光,“阿淑,人心难测。”
春日的阳光零碎地洒落在玄衣少年尚未长开的眉眼上,却泛不起一丝暖意,倒透出几分不近人情,杨淑头次发现裴裕不茍言笑时,眸色深沉专注,眼角那颗红痣越发清晰分明。
他若是进士及第,大抵也会被钦点探花,杨淑没来由地想。
事发
事实证明,不是裴裕丧心病狂,而是贪官污吏丧尽天良。
清明未至,空中已经飘起了润物无声的细雨。杨淑一行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沿着水流越发湍急的新安江,一路西行北上,很是断魂。
千岛湖笼罩在一片氤氲水雾中,影影绰绰,依稀可见不远处残破的大坝。
杨淑急着凑近观察,一夹马腹,骏马会意,加快了步频,奔至一处交叉路口,与一队官兵狭路相逢。
杨淑险些没勒住马。
为首的官兵正对着马鼻子,一人一马面面相觑片刻,他才倒吸了一口气,退了一大步,破口大骂:“你她娘的出门没长眼睛吗!”
杨淑不愿在中途惹是生非,拦住裴裕拔剑的手,主动下马赔礼道歉:“冲撞了官爷,小女子给您赔不是。”
官爷见她认错态度良好,面色稍缓,只是嘴上还在不饶人地发牢骚:“我们可是奉县衙之命,护送重要物资,撞坏了你赔得起吗?”
裴裕忍无可忍,回了一句:“什么物资那么金贵?”
官兵刚熄灭的怒火“蹭”
地又上来了,“口出狂言、不识好歹的竖子!”
杨淑劝道:“官爷莫气,他是我的随从,在乡下呆久了,没见过世面,官爷别和他一般见识。”
莫名其妙变成孤陋寡闻的下里巴人,裴裕眼角抽了抽。
“我们专程护送加固堤坝的砖石和泥浆,事关民生大计,耽误了,你们担当得起吗!”
“你们当真是去加固堤坝的,而非另有图谋?”
裴裕面沉如水,潮湿的空气中隐约透出几丝硫磺的气味,他不假思索地拔剑划破罩在手推车上的麻布,动作之迅猛,令一众官兵完全来不及反应。
麻布破了一个大窟窿,露出血淋淋、赤裸裸的残酷真相。杨淑眼皮狠狠一跳。
官兵首领气急败坏:“真是反了!狗胆包天!”
“是谁狗胆包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