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小说网>前夫是个真黑粉 > 第 42 章 042(第2页)
第 42 章 042(第2页)
晋国的皇帝和定安王前年曾来过一次,那一次就曾让满朝文武心有戚戚。扶薇花了很大的心思,才将“贵客”
送回。
如今又要来了吗?
扶薇看完信,将信笺悬于烛火里烧毁。
宿清焉从外面进来,看了一眼扶薇手中正在燃烧的信,他收回目光,并不好奇。
他好奇心向来不重,这倒勾着扶薇心里生出好奇。她燃尽最后一点信笺,将信笺最后一角至于香炉中。她托腮问宿清焉:“你瞧见我几次烧信,都不好奇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吗?”
宿清焉微笑着,道:“既是给你的信,你看过烧毁也没什么奇怪。”
扶薇追问:“你就不好奇是什么人总是给我写信?”
宿清焉想了想,问:“你弟弟?”
扶薇轻“嗯”
了一声,轻叹:“一猜就猜到了,无趣。”
灵沼从外面进来,禀告扶薇沐浴用的热水已经备好了。扶薇起身去浴室,经过宿清焉身侧的时候,状若不经意地探手,指尖儿在他的手背轻轻划过。
她已走远,宿清焉垂眸,望向自己的手背。手背上似乎还残着一丝酥意与柔香。
宿清焉的突然回来,打断了扶薇的思绪,她泡在热水里,不由皱起眉陷入沉思。
她知道确实到了该回京的时候。
这段时日,时光如水匆匆而过,她一直没有去想归期。可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永远推迟。
扶薇想起前几日宿清焉随口说除夕时给她做个特别的花灯。要不……过了除夕再启程吧?
扶薇沐浴之后回到寝屋,坐在炭火盆旁,将半湿的长发从一侧肩头垂落下来,烘烤着。
宿清焉走过来坐在她身边,动作自然地拿着巾帕给她擦头发。
()柔红的火光闪烁,扶薇脸颊上一片暖意。
“薇薇,快过年了。”
宿清焉开口,“我们回家吧?”
扶薇微怔,继而缓缓蹙眉。
“已经出来这么久,是该回家了。虽然母亲知道我还好好的,我也写了信回去。可是过年时,仍不舍得留母亲一人守岁。”
宿清焉微笑着,温润道:“等过了年,我再陪你去别的东西四处走走。春暖花开时,各地景色必然比眼下的冬日更多彩绚丽。”
他温和的声线擦着扶薇的耳畔,扶薇听着他向来能够让你心暖心安的语气,心里却乱成一片麻。
还是要回去吗?
她宿流峥那些不堪的事情,还是不可能一直瞒着他,对吗?
也是,这世上根本没有永远的秘密。
“薇薇?”
宿清焉轻声唤。
扶薇抬头,已经烘干的青丝从宿清焉掌中如丝似缎滑走。
扶薇静静望着宿清焉的眼睛。
他这双眼睛永远干净澄澈,有瑕之人望着这双眼睛,甚至会心生愧意。
宿清焉立刻道:“若你还有别的安排,也并非一定回去。不管如何,我都陪着你。”
扶薇只在这一件事上不够坦荡。这种不坦荡,让她午夜梦回望着睡在身边的宿清焉,时常自我厌恶。
她因为眷恋宿清焉一时的好,而当了不敢承认的卑鄙小人。可她不能一直逃避,也没有打算一直瞒着宿清焉。那些错事,总要面对。
扶薇笑起来,她说:“好啊,我们回水竹县。”
宿清焉松了口气,道:“等去了万福寺,再歇一日,我们就启程。路上不要太匆忙。我算了算,腊月二十五六可以到家。”
扶薇轻轻点头。“你安排就好。”
她靠在宿清焉的肩头,凝望着炭火盆里不断升起、卷动的火苗。
扶薇微微失神。
她突然松了口气,觉得这样也好。既然她早晚都要离开宿清焉,让他看清她的真面目,也挺不错的。
夜里,扶薇又做了噩梦。
梦里,是家人哭天怆地的嚎声。到处都是鲜血,到处都是躺在地上没了知觉的人。她哭着往前走,在一地的尸体里走得踉踉跄跄。她一不小心被绊倒,白净的小脸蛋立刻沾满了鲜血。她转过头看去,看向绊倒自己的尸体。
她认出那是乳娘的面容,她哭着伸出小手,使劲儿去蹭乳娘脸上的鲜血和脏泥。
“醒醒、醒醒,阿娘你醒醒……”
她一边推着一边哭。
父亲忽然抱过来把她抱起来,一边抱着她往外跑,一边捂住她的嘴巴叫她不要哭,不要被人听见哭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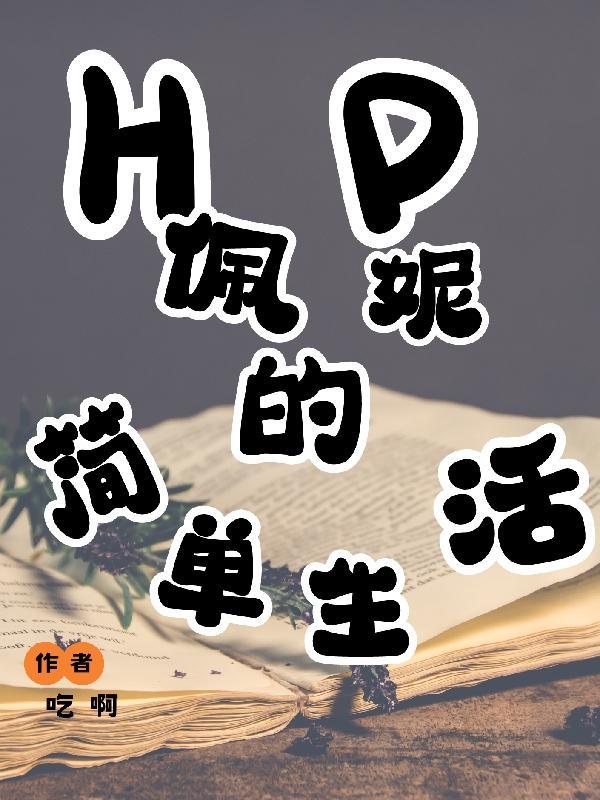

![[演艺圈]死灰不复燃](/img/2337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