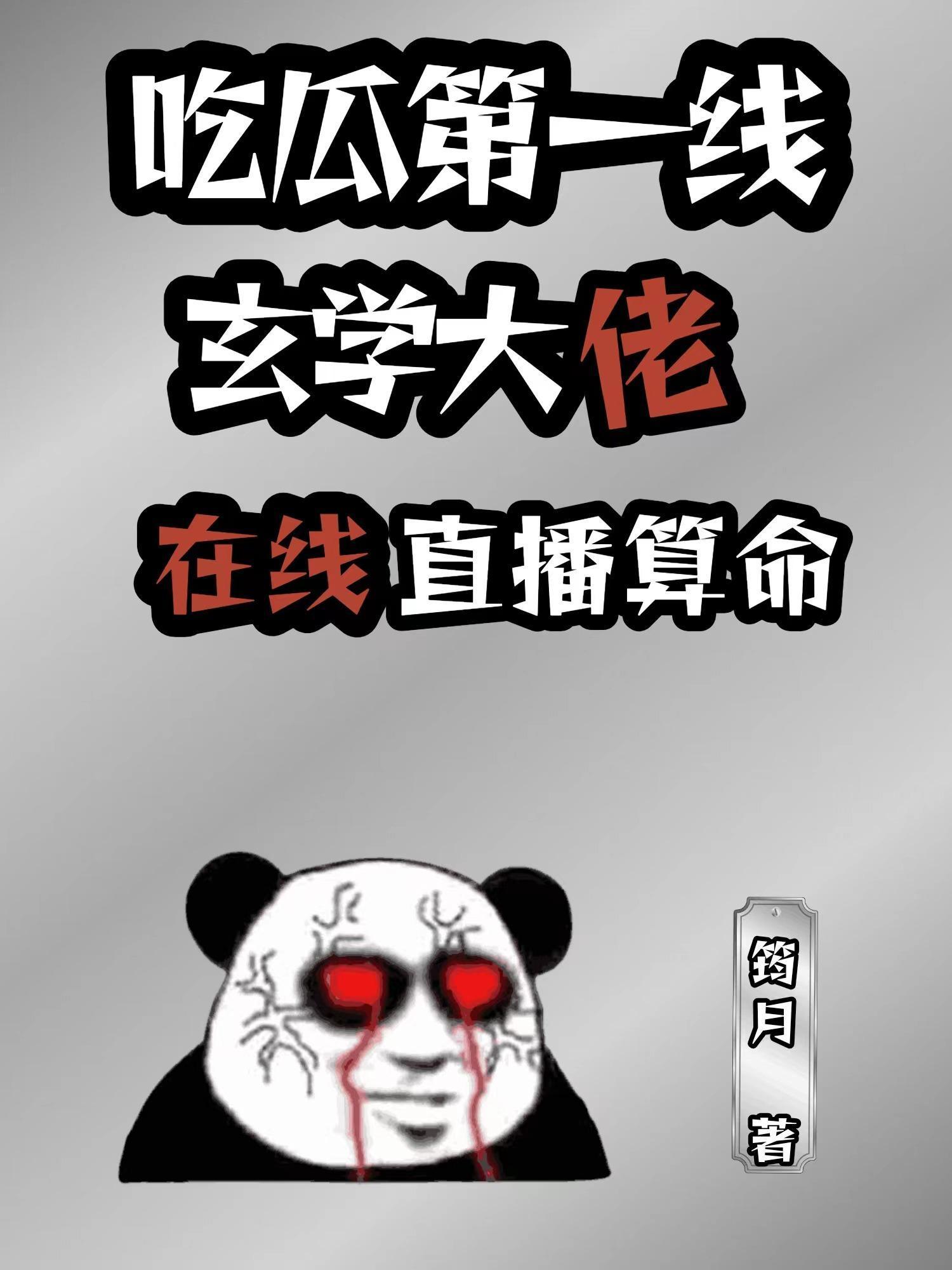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夫君废了之后 > 第32章(第1页)
第32章(第1页)
他轻咬她的耳垂,病态呢喃,“乖一些就好。”
他真想拔掉她身上的刺,用红线将她束缚,永远做他掌心乖巧的花。
难眠
沈绥今日穿着官服回来的,竟然都没有来得及换。
离开她片刻,他褪去官服后,露出里面的黑色交领长袍,衣襟用金线绣着松鹤纹路,衣襟口袒露着好看而长的锁骨,身上有种淡而冷冽的木香,应当是回来前熏了冷香,毕竟早晨不曾听见什么动静,也不曾闻见什么香味。
他靠近的时候,乌春不自觉身子往后缩,将要离他远些,又被他另一只手按住了背,手指恰恰落在脊背正中的沟壑,天气渐热,衣衫单薄,隔着布料也尤其明显,他从下往上,顺着沟壑抚摸……
又从她脖颈一路辗转吻上去,像毛绒的芦苇一下下挠她。
乌春的手指一点点抓紧了他胸口的衣襟,没什么好气,“沈辞宁,你能不能快些,若是无事,可以去查案子,也可以去研究雕琢你那些玉石头,总之别在逢春殿。”
沈绥是有个少有人知的爱好,他喜好雕琢玉器,宣阳殿里头专门有个摆满玉石和刻刀锤子的架子。经他之手,粗糙不平的玉石被打磨雕刻成雕花玉佩、小巧扳指,便是专门以打磨玉器为生的匠人,都未必有他手巧。
他的手掌便有层薄薄的茧子,食指和中指的骨节侧也带了茧。
染了满手血腥,却偏偏喜欢最纯洁无瑕的君子之物。
乌春前世总盼着沈绥能雕支玉簪送给她,可惜直到死都没有。
沈绥闻言,薄唇微抿,“少说些这种话,毓宁宫是我的宫,这里每一寸土地我都去得,逢春殿自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且你是我的妻子,我要同你做什么也天经地义。”
乌春的眼里却毫无情动之意,手往下探,而后五指收拢。
同时,沈绥的喉结滚动,喉间闷出一声粗喘。
乌春眼中那丝嘲讽与淡然像是一把刀,轻轻一挑,就能戳破他心里那些流光溢彩的泡沫,于是只剩下了黑暗与冰冷。
她手指灵巧,他额角青筋直跳,胸腔之中浸出些疼意,他变了脸色,咬牙切齿,“你既然如此痛恨我,当初为何又要……”
他环绕住她、叩在桌沿的手几乎将合欢木掐出指痕,青筋狰狞,嘴唇张了又张,却终究将接下来的话生生咽了回去。
乌春不卑不亢,“当初怎么了?你又是怎么待我的?”
“我待你不薄!”
他竟嘶喊出口,一双眼里的怒意如蛛丝网攀爬。
乌春亦厉声道:“那你知道什么叫喜欢、什么叫爱吗?!”
他张开嘴,却在半空中哑然,见状,乌春笑了,不再同他多说,觉得没什么意义。
难道一辈子不够,还要再断送一辈子的自在,信他真会爱她、敬她,然后困在他身边吗?
沈绥反问道:“你呢?你对我有没有喜欢、有没有爱意?”
话问出口,他自己却微微怔忡,她有没有心悦他,重要吗?她的心意,能为他换取些什么?她的爱意,对他的大业有什么用?又为何会问她这种问题?
乌春道:“若我说有,你不会在意;若我说没有,你只会恼怒。既然如此,又有何问的必要?”
像是有一盆凉水灭顶泼下,沈绥胸腔中熊熊燃烧的怒火霎时间熄灭,他的手捏成拳头,指甲陷入血肉,良久,说不出一个字。
好似她说得对,他确实会有此等反应;又好像她说得不对,因为她太过轻描淡写,往他心里扎了一根刺。
见他渐渐平静下来,乌春弯了弯膝盖,“殿下请回罢,逢春殿这两日都不必来了。”
说罢就从他身边错身而过,走向院落,一拐,没了身影。
空留下沈绥僵站在原地,思绪烦乱,对着外面一地落花残红,两相无言。
……
乌春其实没有远去,站在一棵粗壮的树后,望着朱红宫墙,心下叹了口气,也不知何时才能突破这层层重围。
海棠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落下的花朵了。
不知几时过去,等到望见沈绥离去的笔挺背影,她才从树后走出。
沈辞宁,你我终究是做不得寻常夫妻,是前世的奢求,也是今生的不可能。
我想要的东西,你从来就不会给,也给不了,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
两相纠缠,又有何意义?
……
乌春走入库房收拾东西,将下蛊要用的材料放到一边,带了牛皮手套,将几只死去的干枯毒虫扔进陶瓮,再打开一个小翁,立刻有“嘶嘶”
声响冒了出来,一条青绿的小蛇蠕动,鳞片泛着游动光滑的光。
乌春捏着蛇的头和尾,放入装好毒虫的翁中,再盖上盖。
本该是放入七八只毒物,取最后活下来的一只,但那样毒性太强烈,恐怕稍有不慎就要惹祸上身,就选了较温和些的炼蛊的方法。
选毒虫也是有讲究的,要既有毒又有药用作用的,这样就算被揭发也好含糊;还要毒性只有三分的,否则毒死了竹叶青,那可就养废了,最好还能缓和些竹叶青的毒性,让中蛊之人不至于立刻死去。
唤来阿贵,将翁递过去,瞧见那太监一副哆嗦样,乌春不由笑道:“莫怕,这翁盖得可严实了,又耐摔,只要你不乱打开,就不会有事,再说了,你若有事,本宫也可救活你,有何好怕的?”
阿贵颤声道:“是,奴才遵命。”
“埋在毓宁宫东南角的土壤下,十日之后再原封不动挖出来,按照本宫说的做,将本宫给你的所有东西,都交给那人。必要的时候……”
乌春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锦囊,交给阿贵,“可以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