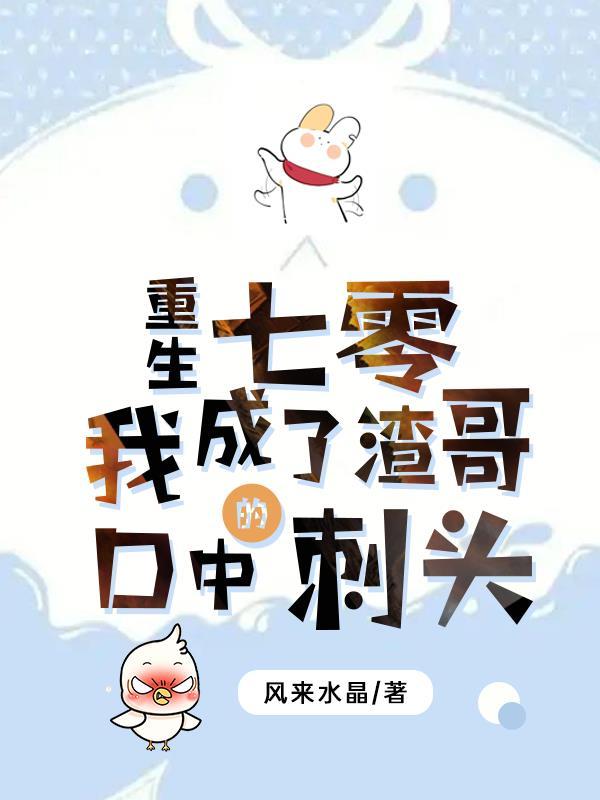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海姆达尔什么水平 > 第90章(第2页)
第90章(第2页)
卢辛达呢?
明明大家一起躺在垃圾堆里,四叉八仰,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
宝琪说,“最开始,是他先约我出门的然后他喝醉了,我掐了他。”
——我掐住他的脖子,差点掐死他。这种危险的活动让我明白我已经不再是游戏场的服务员,我和人一样。
——暴力、杀戮,跨过道德的边界,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怖的自由。
机器睁大它那双漂亮的眼睛,作出惶惑、热切、恐惧的拟态。
包庇乱象
当机器关节开始弯曲,手掌缓慢贴合生物的脖颈。它开始用力,大拇指往上推。机械躯干倾斜,将重量通过弯曲得嘎吱作响的手肘压在掌中生物的骨骼上。
机器关节发出响声,人类也一样。
不同于叫喊,一切喉咙能够发出的生物性质的声音早就在暴力行为中被禁锢消除,剩下的只有有机体本身身体的呻吟——不混合任何精神的、纯肉体化的呼喊。
就像舞台上的黑猫一跃而下,带着露水、钻石、黄金;怨恨、恐惧、狂热——时代的魔术师挥舞一下指挥棒,无数奇思妙想就从他敞开的大脑蒸腾而出。
在巴特拉各亚的梦境里,一口湖泊正在沸腾。
夫人从宝琪的眼中读出机械生命初获自由时天真又残忍的感触,又惊讶于它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的破坏欲——是人类将它调校得太好了。
“你会背叛我吗,宝琪?”
领袖夫人突然问它。
此时,狡猾的机器回答道:“我永远效忠于您,夫人。”
夫人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机器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小姑娘。被她强迫着穿上蕾丝重迭的裙子,走到她面前,像一只用来展示芭蕾的人偶。
不对,第一次见到宝琪的时候,它就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现在也一样。
机器在思考,在体会,在发现自我。它的人生不需要真理和规律,因为它不像人那样渴望死亡与不朽。
死亡在城镇里紧贴人类身后,但是机器是懒得去看它的,它们是不必看、看不见的。
就像一些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东西一样。
夫人摸了摸机器柔软的头发,她想说:去吧。
但是,乌尔多尔紧接着又陷入迟疑——奥玛极度危险,至少对宝琪来说是这样。
这个家伙作为高塔隐隐扶持的“替补领袖”
,天然就跟宝琪、跟领袖对着干。这个男人就像一只老鼠,夫人当然可以找到他,只要顺着他的老鼠子孙,找到它的洞穴,就能轻易杀掉这只老得快成精的脏东西。
但是,然后呢?
让下城区的老鼠们再推举一只谁都不熟悉的新鼠王吗?
城镇建立在微妙的平衡中,乌尔多尔不想打破这种平衡——这也不代表奥玛可以伤害她的心爱之物。
“先去联系迪亚斯,”
夫人说,“就在我这里打电话,我要看着你联系他。”
宝琪拿起话筒,拨通上级办公室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