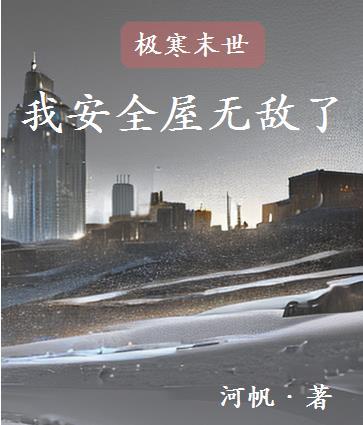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景明春古言 > 第87章(第1页)
第87章(第1页)
许是方才言语有些激动,云静忽然感到一阵晕眩,不禁伸手摸了下后脑。
元珩探过身去看,“怎么了?”
她告诉他摔过马车的事,元珩预感不妙,得想办法赶快离开此处。
幸巧,刚把衣物收拾好,就听见了林衿的鸣镝。
他把云静抱出了洞,朝着鸣镝方向翻过山坡……
天幕不停地变幻色彩,泼了墨的穹顶洗澄至月白,又浸在日晖中染了金,忽又被赭红砂漂成了艳霞。
云静仿佛在睡睡醒醒间,过去了好几日。
她记得,林衿与几名死士找到了她和元珩,两人被藏在运送溺物的水车里入了城。
恍惚中,好像有太医来过,丹蓉喂她药时,说她颅后虽无明显外伤,但内有淤血,幸而不严重,需静养几日。
她只是觉得累倦,不愿起身,昏昏沉沉中,她每次睁眼都看见元珩坐在榻边,问她身上还疼不疼……
这日再醒来时,她明显觉意清爽了许多。
挑开纱帏,见窗外夜色朦胧,暖阁外间的烛火莹烁,也不知是什么时辰。
她披上外氅刚出内室,就听见丹蓉和水韵靠坐在屏风下窃语。
“听说是代王跑到陛下跟前一顿诉苦,咱们殿下这才被禁了足。”
“哼,恶人先告状!要不是殿下及时出城相救,主子怕是早就死在刀下了!”
云静惊疑道:“殿下被禁足了?”
两婢女蓦地一惊,从地上爬起,“您醒了?”
云静急问:“殿下是因何事被禁足?”
丹蓉道:“您被困城外那日,殿下为闯城门,与豹骑卫起了冲突,陛下以‘滋扰京畿安防,殴打高阶武将’之罪,命殿下在府中禁足十日,现已过去五日了。”
云静不语,立即转身推开阁门,奔去了永晖堂。
迈入书房,她看见元珩正坐在案前运笔行书,沉静的模样令人不忍进去打扰。
云静就这样站在屏风后望了他片刻。
他没有束发,窄袖衫外随意披了件墨绒氅,硬朗的侧颜半掩在虚淡的烛光下,流畅的悬腕走笔好似拂去尘世浮华。
“又不进来?”
他忽然开口。
云静一怔,从屏风后绕出,走到他身边,一想起他被禁足就气的牙痒痒:“此事本就不公,代王对你我痛下杀手,却是你在受罚,哪有这样的道理!”
元珩没有答话,反抬眸打量她的脸色,关心问:“还难受么?”
云静神色柔缓下来:“好多了。”
“中正定品耽搁不得,父皇不会罚我太久,十日而已。”
元珩放心地淡笑。
其实,元瑞告状后,禁足之期本是一个月,因陈言中以吏部政务紧要为由,为元珩求情,才减至了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