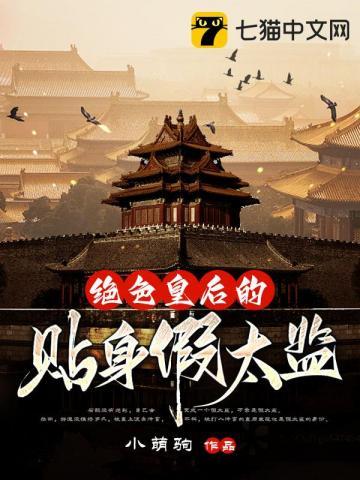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少年短歌行电视剧免费观看全集高清 > 第76章(第1页)
第76章(第1页)
江玄似笑非笑:“什么意性,我倒是不懂了。”
“你不懂,我倒懂了。你心仪这小公主,只因你们俩是同道中人。说得好听点,算是至情至性,说得难听了,那是自己拣的路,只肯一径走到黑,碰到鬼都不回头!”
“哦,你是说我意气用事。”
“随你吧,反正是你的家业,你的意气。”
江玄闻言,笑意有些迂回苦涩:“不是我的家业,是江家的。”
渭川微微一愣:“到现在你还……”
江玄仍悬着他那一抹似是而非的笑意。
渭川问:“你是为了她做到这步田地,还是你……”
“我不光是为了她。只是,我不会为了江帮、江家,牺牲她。”
“你有没有想过,倘若她要利用你,借江帮之势力呢?”
江玄笃定地摇摇头:“她不会。”
“只怕人心难测。”
江玄微微点头:“你说的对。人心难测。我从前不喜欢似玉汝那般,动辄扶额晕眩的病娇儿,可见若是她发病,我却心慌意乱;我从前不喜欢女子蛮横,可若是她不讲理地闹意气,我倒觉得她性情可爱率真;我从前也看不上轻功那点三脚猫的逃亡功夫,可落在她身上,我又觉得这门功夫实在是好。我闹不清人心是怎么回事,玄而又玄,众妙之门,想这情字,也是玄中之盛,不可轻易解释定论。”
渭川扶额,一脸苦相:“别情啊意啊的,听得我难受死了。你……你真要说,你对着那谁说去,别在我这儿酸溜溜的。”
江玄收敛了话头,又问:“对了,我叫你派人查的齐舒穆、齐世武父子,有什么消息?”
“宅子外守得很严,他们没再来过。鬼绝之侠满寒空从来缥缈如风,没人知道他住在何处,有无亲眷,但听说,他身边有个老仆,唤作‘阿武’,从前帮他传过讯的,不知道这个齐世武是不是就是这个老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他身边。”
江玄轻轻念着“满寒空”
的名字,暗问:“你说,江家同这满寒空,真会有什么渊源么?以他‘鬼绝’之名,真想来一探圆水园,倒也不必费什么工夫。再说到给母亲下毒这件事,就更说不通了。”
“大当家不是不让你再查这个事了吗?”
“这件事太过蹊跷,自鬼门关走了一遭,母亲竟按下不提。我想不通,也放不下。你把这齐家父子二人的画像,给过清风明月楼没有?”
“给了。他们说来定酒宴的人,就是普通模样的两个江湖人,不是画里的人。”
“模样再普通,也不至于找了这么些日子都没影。怕是易过容的。”
江玄思索片刻,“看来只能从毒上下手,这观音露,你让秘帮的人盯牢了。”
“好。”
46任家坊旧事(一)
阿元在园子中,舒活过手指,手中拈着打磨染色过的一手帕子小彩石,脚下来回踱着轻功步伐,随着身影横行如风,一道道石影便自池子上假山的漏透处一一掠过。
今日品儿被后厨杂事绊住脚,来得晚了些。
阿元多练了半个时辰,身上微微出了汗,开门时面颊渗出艳色来。
品儿端着食篮发着呆。
阿元接过她的食篮:“愣着做什么?”
品儿回过神来,忙帮着将菜布出来,憨傻之气溢于言表:“姑娘只消擦得这么一点胭脂,简直好送入宫做娘娘了。”
阿元伸手擒过一双筷子,闲闲随口道:“娘娘也不过一日三餐,一眠数尺,你们倒为什么想着做娘娘?”
品儿的脸上现出无限欣慕的样子,直直往高不可攀之处望去:“哟,姑娘怕是不知道。这娘娘的日子,过得多舒坦呀。多少衣服首饰,戴不过来呀,成群成群的丫鬟宫女,都跪在脚下服侍,再说那个御厨做得的好菜,香得人牙馋嘴馋肚皮馋,就没有吃够的时候。反正我娘说了,这娘娘过的日子,就跟神仙过的一样。”
“神仙过的日子?”
阿元讽刺一笑,一双睛目如空心琥珀,“神仙不会死,可这皇帝娘娘,照样得听阎王的鬼话,未必是个好死。”
品儿早已习惯阿元时不时语出惊人,并没过多说话。她白日常同后厨人说,这女大夫t好是好,就是偶或有些颠来倒去的怪话,叫人弄不懂。
品儿见阿元低头专心吃食,便拿新近的听闻告诉阿元:“姑娘听说没有?”
阿元心中好笑,这小丫头,每次都是这一句开场白。她这园子,平时只这送饭丫头来得多,她还能从哪儿道听途说去?
“说那王家两位老爷,领着两位小姐,今日便要回苏阳郡了呢。”
“因为魏小姐落了水?”
“不知道呀。反正我妈妈说,这会子,这映雪呀,雪化了;这素岚呀,岚气也被吹跑了。咱们园子,一时半会又没婚礼热闹可看了。唉……”
没了婚礼热闹,便没了大半年的说资,品儿同江府的许多下仆都十分失望。
阿元闻言,不自觉停歇了筷子,有什么意念空空地在心头一转:又或者是魏玉汝占了鳌头,成了魁首呢?如此一个念头上来,便常驻脑海,挥散不去似的,连带魏玉汝那句娇软软、温意意的“玄哥哥”
,也似回荡在耳边一般。阿元如闻魔音,掩住了双耳,脑中又无端现出“琴瑟和鸣”
“举案齐眉”
的字眼来。
品儿见她神色大变,忙凑到面前问:“姑娘怎么了?”
阿元竭力抛却脑中魏玉汝与江玄的画面,放下掩耳的手来,定睛一看,方才手中的羹汤早已洒了,汤碗打着旋儿落在石子路上,自己的半幅裙面也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