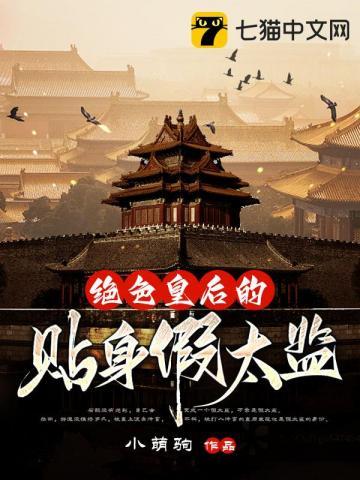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少年短歌行在线阅读 > 第82章(第1页)
第82章(第1页)
“可观音露,还有你的轻功师傅,还有……”
“我自己也会找的,老头儿,还有那个拿了我观音露的人。”
阿元拨弄着地上的泥,将夹竹桃的落花瓣埋了起来,“我会同你母亲说的,不会叫你为难。”
江玄忙道:“哦,我母亲去了外县,得等些日子。”
阿元连眉头也没皱一下:“那也好。我留封书信,今日就走。”
江玄大为惊讶,亦是大为光火:“今日?你今日就要走?”
“我来,本就是替你母亲治病解毒。她都大好了,我没有留下的理由了。”
阿元将一地落花埋了,掸去衣上浮尘,垂睫沉沉,轻道,“江玄,多谢你,初入江湖,能识得你这样好的人,我很开心。我这人个性古怪,望你原宥我从前种种,以后若是有缘再见……”
阿元说到此处,竟不知有缘再见该如何,把酒言欢?秉烛而谈?亦或只是抱以一笑,擦肩而过呢?
江玄低着眉眼望着她:“若是我……我不想让你走呢?”
阿元眉心微蹙,道:“我留下做什么?”
江玄早见识过阿元说走即走的本领,连南越王寨,她也没有再多停留片刻,她此刻已说出口,绝不是轻易可回旋的。
江玄想至此,再不犹疑,上前一步扶住阿元的双肩,他的眼角有一颗痣,像是欲流未流的一颗泪,他的目光泓泓,静水深涌:“你留在我的身边。”
江玄的手是暖的,他身上的暖意也渡到她身上,笼住了她的身心。
江玄眸光微颤:“说来你可能不信,这些日子,我时常做同一个梦。梦中有月,有竹,还有……还有……”
阿元的目光随着眼睫沉下去:“要你运功救命的病秧子?”
江玄神色一顿,仍想继续说话,阿元推开了他生着暖意的手。江玄倔性一起,丝毫不顾忌君子廉耻,仍是生生按住阿元的双肩,阿元越是挣扎,他的手劲越发不受控:“病秧子又怎么样,我愿意救你,你发病百次,我便救上百次,等为你耗干这一身归藏功,你便算知道我的心了!”
阿元闻言,十分诧异地看向江玄:“这……这不像你说的话。”
江玄的手劲松下来,目光也跌败下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话能留住你,我便说什么。”
阿元从来是被救者,江玄是救她的神、佛、圣、仙。可这一刻,江玄跌落了,他为她跌落成一个最最普通、最最堪怜的求爱者,囿于情与无情的困局,无处寻得解脱之法,也丝毫不愿意解脱。
眼前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江玄于她有情,而她于江玄,亦是藏于心,而缄于口。女帝已经拿皇外祖的例子对她训诫过太多次了,这情爱是世上最深的陷阱,最毒的利器,他们想重掌河山,征服毒水河外的辽阔疆域,必须断爱绝情。他们是为收复山河而生的死士,皇外祖楚渊丢掉的一切,他们要从楚苻身上夺回来。
阿元恍恍惚惚地想着,惊觉自己又被女帝主宰了思绪,脸上现出惊恐的神情。
江玄轻呼道:“阿元?阿元?我吓着你了是不是?”
阿元忽的一把抱住了江玄,像溺水之人抱住浮木般,伏在他肩上饮泣:“我不必听那人的话。我可以有情、有爱、有家的,是不是?”
江玄心念忐忑,又不忍细问,只得应道:“是,是。”
阿元哭了半晌,江玄便也抱着她,由着她。
好半天,阿元止了哭声,想从江玄怀里出来,谁知江玄仍抱着她不放。
阿元忽起了羞赧之意,轻道:“我好了,你放开我吧。”
江玄轻轻一笑,他眼中喜悦的波光,将眼底的那枚泪痣衬得像碎金:“这一曲《凤求凰》,我可求到了?”
阿元侧脸看着那笑意,心头突然闪过一阵寒意,慢慢推开他:“我听不懂什么求不求的。”
江玄喜未过半,又转忧色:“你不能总这样,好一会儿,歹一会儿。阿元,对我说一句实话。”
阿元面上的泪痕干了,少女的稚嫩与无措褪去了,一种与母亲楚望相似的冷酷渡上了她的眉梢眼角。
“实话是,我还是要走。”
江玄揣度她神色:“你是说,我们彼此有情,你也还是要走?”
阿元轻轻道:“是呀,咱们彼此有情。可我不做人家一群姬妾中的一个。”
阿元说着,拨开了江玄的手。
江玄忙道:“我怎么会令你做姬妾?我也没想过要娶别的人。”
阿元并不相信,只说:“我也没那么天真。江帮少主,难道会娶一个毫无身份的采药女做正妻?其实,其实你母亲,私下找我说过了。只不过我那时候以为,是她老人家一厢情愿在说胡话。”
江玄大为惊骇,若是母亲出面,她们谈话的内容,可想而知了。
阿元继续道:“女帝早同我说过,我的婚姻必须是一场最划算的交易,若能牵扯到当下的朝堂势力自然最好,否则,只好嫁给越扶疆了。我想,你的婚姻,也不外如是。”
江玄一双眸子笃定:“可你没有嫁给越扶疆,不是么?我们不是傀儡,至少你和我,都是不愿做傀儡的人。”
阿元抬眸望着他:“你是说,你要同你的母亲和家族反抗,只为娶我?”
“我母亲会谅解的。”
“可我不是一般平民女子。”
阿元眼中琥珀烟盛,情绪难辨,“我的身份,会为江帮带来灾难。”
江玄似笑非笑望着她,也学了她难以捉摸的那一套:“你说自己是阿元,嫁给我便是江元,是我的妻子,再不是其他人;若你说自己是楚一凰呢,掀出了你的身份,咱们便去南越占个山头,我瞧着南越山清水秀,很适合去过神仙眷侣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