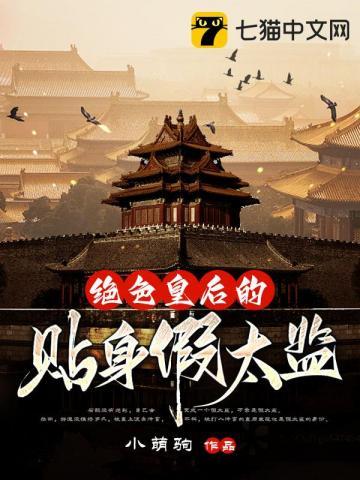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啊这里是规则怪谈晋江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至于我,他答应我的已经做到了,他把之前我经历的所有谜底尽可能详尽为我做了解答。
“……”
我看了一眼闫默就咬牙快速道:“我还有个朋友在下面。”
他与我对视,像是明白了什么,眉头紧锁,对我坚决摇了摇头。
我知道他是对的,张添一应该也不希望我做无畏的冒险。
但是,有个声音来自于我无法控制的那一部分,冷静对我自己说:
张添一确实不愿让我去,但他知道我这人是多会作死的。
只要我有万分之一冒险的可能,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做两手准备,在底下为我留足够的线索,甚至是一条可以撤退的生路。
电光火石之间,我猛地挣脱闫默救助我的手,用力咬牙闭眼往下一坠,立刻就有强烈的推背感把我压入深水。
原本还有些回暖的水流似乎在上方分层了,刺骨的寒冷顿时袭来。
我在冰寒的水里被杂物来回撞击,喝了不知道几口水,手里死死捏着矿灯没有脱手。
湖水的清甜在此刻变得格外怪诞可怖,我默数着心跳声计时,任凭自己在水流裹挟中飞快下潜。
像是乘坐着某个失事电梯,一具一具陈年的浮水尸在我上方掠过,直木般悬停着,把偌大空荡的湖水分割成了无数个细小的格子间。
最近的距离,我甚至可以清楚和浮水尸凝固死白的眼珠对视,看到有同样丝丝缕缕的气生根在他们的眼眶和耳朵里爬出漂浮。
而再往下,水体之中就变得清净起来。原本此间同样漂浮的浮尸不知所踪。
明明只是数十个呼吸的下沉,我就明显感到了不同。
岸上伙计们的呼喊声完全消失了,似乎我们之间已经被阻隔开了无限远的深度,剧烈的乱流中四周是无比的寂静,连带着我像个发亮的陀螺旋转时也是无声的默剧。
极动到极静的反差叫人吐血,我被水流卷到了那些树根中心,到处全是一道一道的黑色交错。矿灯的光线在里面胡乱扫开,能见度很低,就看到我自己的手背,在灯光下透出的血管也变成了一种青色。
激荡的水流和漩涡到了这里,拍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树根上力道就开始分散,同时四周的水,不知道是我逐渐适应了,还是寒冷过度后感官失调,似乎又恢复了些许温度。
只是,那颗“石头”
呢?
背后连着我的树根变得十分温顺,我举目四望,扒在那些树根上借力,到处除了漆黑的水似乎什么也没有。
我感到后背那种痛痒减轻了,下意识探手去扯了一下,这次触手所及非常绵软,那些树根轻易就脱落下来。
我猝不及防,手里就抓了一把已经软踏踏的“黑发”
,肺里立刻有些发刺。这一下我就不敢再去动脑后连着的那几根鬼东西里,扒着树根行进间异常小心,像呵护我的生命线一样,注意不让我脑后的“小辫子”
受损。
而那些已经被我扯下来的部分,慢慢就化开,变成一种类似啫喱或者泡开藕粉的质地,接着快速发黑腐烂,变成了腥臭的绿水,一下子在水中被稀释消散开来。
我注意到那点颜色在水中消散是有方向的,试着把手伸出去,在手里静静放了一会儿,半晌,才感到似乎有微不可见的气流,方向就在我脚下往上吹。
可脚下似乎也只是黑压压的水。
我回想起当时看见石头豁口的青色,提灯在树根中穿行,继续往下潜。
但是没有,所有的色彩此时消失了,只有我本身的血色在深水中散发着幽幽的青。
和刚才疾风骤雨不同,此时的寂静和单一的黑色,带给我的是更深的不安和警觉。
唯独我具备的光亮和色彩,在静默的水中实在太显眼了。
如果水里除了浮尸、那个“石头”
和树根,还有别的什么,我无疑就是脑门上竖着个大喇叭欢迎人家来加餐。
但不得不承认,在我的心理准备里,即使真有什么怪物邪祟也是可以接受的。
偏偏现在什么痕迹都没有,似乎是无声嘲讽我,让我可以打道回府了。
奇怪,难道连带着这场格外突兀的暴风雨,所有变化都只是一种巧合,是我自作多情了吗?张添一那厮也真就绝情到没有给我留任何引路,不在乎我这个老弟死活了?
我没泄气,只是费解,索性又停下来,再次尝试捕捉那股微弱的气流在不在。
又不知过了多久,久到如果没有那些寄生的树根,我多半早就已经淹死泡烂了,手掌上才感到近乎幻觉的吹动。
还是在脚下,而且越来越微弱了,弱得像是有人在我耳边轻轻吹气一样。
那是什么,底下有个空腔或者地裂吗?那为什么会变弱?
此时没有线索可寻,我再次下潜,因为水压就感到整个胸膛和肋骨都包裹着一种隐约的压迫,知道不能过久耽搁。
这一次,比幻觉更轻微的,一点青色晃过我的眼睛,立刻消失了。
同时,那种从上而下的气流也再没有踪迹。
我按着在深水水压中逐渐不适的胸膛,镇定下来,先自问自答了两个问题。
第一,目前这些还和陷坑有关吗?
答,应该没有。因为之前在岸上,我和我哥都互相喊过姓名,没有任何人突然暴毙融化。
既然陷坑和岗亭给我的感觉像是盲人在房间中摸索大象,那么现在如果又有新的怪谈,给我一些似是而非的熟悉感和错觉,那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前车之鉴,我最好不要把之前总结到的任何规则盲目套用进去,最好是把自己当做一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