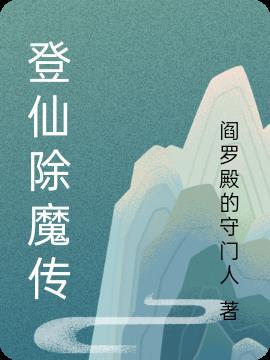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公主请小心百科 > 第118章(第1页)
第118章(第1页)
乌恩其又说:“不是这个还是什么,我亲了他一下?你后面半句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陈雁行虽说对儿女情长没什么兴趣,可她当了许久的歌女,自认为对于那些细腻微妙的情感还是能比别人敏锐些的。在她回忆里,直到她临出发前,乌恩其和裴峋都不像有额外私情的样子。
尽管这两人视彼此为特殊,但陈雁行认为捅破窗户纸还需要一段时间。毕竟这二人出身差异巨大,中间又横亘着两个国家的纠葛,陈雁行怎么也设想不出来他们该如何互相表达。
“你想知道,回头了给你慢慢讲,”
乌恩其见她表情一下一变,就猜到她在想什么,“闲聊这么久,该干正事了。”
陈雁行的回归,让乌恩其收回了一枚强势的底牌。这让她在出手清洗如今的朝堂时底气十足。
不出几天,该收拾的就都收拾了,少部分人留下,大部分人都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离开。
乌恩其懂得什么叫做恩威并济,能以温和手段安抚的,她不会施加更多。而彻底无法为其己所用,威胁极大的,她也毫不手软。
等把朝堂整顿的差不多时,关于她继位仪式的各项事情也开始被逐步提出。名正才能言顺,乌恩其也不准备在这种琐事上和传统观念对着干。
只是导致她迟迟拖延的变数依旧没有出现。
“会不会是那家伙倒台太快,压根就没有残党留存?”
陈雁行问。
“他现在还是暴毙而亡的,又没人去清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而且他之前也没有表现出过想要我来继位的意愿,你觉得难到这种情况下,会可能没有一个人想打着他的旗号造反吗?”
乌恩其已经接手涅古斯全部的事项,正在一桩桩一件件分类分开。
陈雁行抓了抓头发:“那、这么说,还确实不太可能。”
裴峋也在一旁帮着乌恩其做整理,面前的东西一摞摞,堆的能有小山高。
只是乌恩其还需要看一眼上面的内容,裴峋则只需要负责将这些东西再做一次二次整理,因此手头上比乌恩其快了许多。
“你俩这些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
陈雁行忍不住问。
乌恩其忙里抬起头:“打我坐上这个位置的那一天起,我以后的责任就永远不会完成,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
裴峋道:“为君者的确如此,不过殿下也该早些做打算,组出自己的可用之才来。否则不管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身体总有一天会吃不消的。”
“我正有此意,”
乌恩其这下把手中的笔都搁了下去,挺直了腰杆道,“人才肯定是要重新选,毕竟现在的缺口不算小,但……”
陈雁行一头雾水的望着她,等待她的下文。
裴峋却眉头微微一皱:“我明白你心中所想,但这绝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说着,伸出手在空中虚抓了一把:“那些看不见逮不着的,却偏偏最难以去除。”
“或许随着时间流逝,未来会有改变。但我既然已决定要担这个责任,就从我开始,去除吧。”
乌恩其语气故作轻松,表情却十分认真。
陈雁行着急道:“你们别打哑谜了,我和你们又没有这种默契。到底想干什么,快告诉我!”
乌恩其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坚定地说:“我希望这次,能让女子入朝为官。”
新枝
如果拿鹰的眼睛去俯瞰苍生,掠过渺渺的云海,看在那样一片广阔辽远的大地上,人会有多么的细微。
强壮不及虎豹,轻灵不及鸾鹤。寿数有尽不若龟鳌,神通无门不似龙凤。可却偏偏能令枯骨为血肉,化叆叇成朗明,在这冥茫无垠的世上创造出一切瑰异奇秀。
又能使得楼阁倾塌,江河染血,欺良善生出修罗,怀叵测自酿苦果。
乌恩其一直认为人生来奇妙,一个在襁褓中只会哭嚎的婴儿,可能在几十年后成为牧羊人、铁匠,或者一名士卒。也可能拜相封将,封王成侯,谁又能说得上呢?
可对于许多女人来说,她们一生下来就被剥夺了这无限可能的机会,终生都被困在一个小小的框子里。
只能偶尔,很偶尔地抬起头,看向那笼罩在头顶的一片虚无。但却因为在混沌中行走太久,双眼蒙上了阴翳,早已看不清那些流光溢彩之物。
这是一种最无情的残忍,明明同样为人,却被分隔得宛如两种。她们没有权力去掌握自己的人生,只能日复一日地低头,面朝着永远深厚的土地,用泪催生出新枝来。
乌恩其一直在想着该如何扭转这一切,她在心中莫名冲动的促使下,说出了“我希望这次,能让女子入朝为官”
的话语。
裴峋和陈雁行闻言皆是一愣,良久,陈雁行才说:“你这三把火,会烧到自己吧……”
乌恩其说:“我倒是不怕……就怕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帮了倒忙。”
“殿下,我懂您想的,”
裴峋温声道,“但万事开头难,您刚身登大位,自然急切想要做些什么,才觉得不负肩头的责任。但您要在这位置上可不是一天两天,更应仔细考虑。”
“是我太着急了,本以为自己不会再狷急,但果然面对这些大变动之时,还是免不了心浮气躁。”
乌恩其深呼吸了一下,目光旋即恢复了清明。
陈雁行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也没察觉出这二人的相处比起之前有什么不同。
裴峋道:“读书入仕的确是一条能立即改命的道路,但一个读书人的背后是需要倾尽一个家庭的供养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