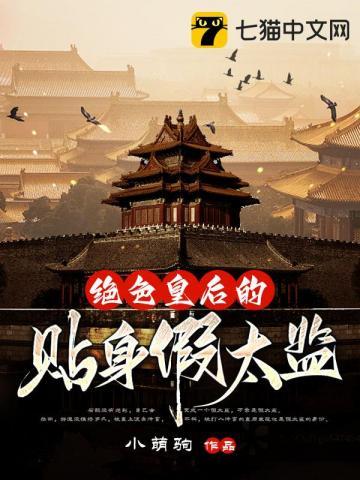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山河之广 > 第76章(第1页)
第76章(第1页)
“你呢,也可以走了。你也看到了,我现在不便待客,衣服进水重得很,迟早把你也踹下去。”
齐同晏一边拧着衣袖的水,一边对四十九说。
四十九一笑,声音从面具后传来:“那我拭目以待咯。”
说着,他的身形逐渐隐去,与黑暗融为一体。
“什么事,和裴伯父喝个酒把自己喝进水池里,倒霉透顶。”
齐同晏嘴上抱怨着,唤来下人烧热水更衣沐浴。温热的水流淌过肌肤,带来美丽而舒适的心情,疲惫被一扫而空。沐浴在热水中,齐同晏不愿再去思考费脑子的事情,只想安安静静地享受此刻温暖。
突然间,他的脑海里闪过某些画面。那时裴壹的母亲也还在,父母恩爱和谐,家中唯裴壹一个独生子,裴家家风正如裴壹父母二人的作风,爽朗却也温柔。裴壹母亲是为救裴沉枝而死的,她下葬的那一天,齐同晏也去了,他还记得裴沉枝捧着他夫人的灵位,向地上倾了一杯又一杯的酒。
那一天,裴沉枝失魂落魄,对月念叨,也对齐同晏与裴壹二人倾诉。他说,家中的将军酒,是夫人亲自酿的酒,因此才会甘醇而余味不散。裴夫人酿的将军酒在当时还剩下十坛,若是一年一坛,今日这酒,只怕是最后一坛酒了。
“等这将军酒喝完了,我就随你去吧。”
裴沉枝当时的喃喃自语,回旋在齐同晏的脑海里。
他猛地睁开双眼,心脏止不住震颤。虽说当年裴沉枝只是因为过度悲伤,一时的玩笑话,此后更是不再提起,可齐同晏总觉得心有余悸。
像是什么东西,冥冥之中自有注定,一切早已安排好。
异珍阁见
那之后齐同晏又去了一趟骁骑将军府,见府上一切安好,没看出来什么异样,这才稍稍放心。
“殿下殿下!我刚刚想起来,异珍阁的管事前两天来送了请帖,说要举行竞拍,我们去吗?”
上京寻常的街道上,繁华一如既往,竹篁跟在齐同晏身后兴奋地问。
“异珍阁?他们这次又有什么好东西?”
齐同晏走在前方,接话道。
“殿下你等等,我找找啊,”
竹篁说着,从衣袖里掏出一卷纸,递给齐同晏,“别的不说,就说这次压台的,上面写着可是谢濯的新作,少女形态的偃甲人。”
齐同晏展开折纸,视线一行行扫过,最后定格在压台之物上,赫然写着制造者谢濯的名字。
“听说这次制造的偃甲人,惟妙惟肖,脸上还上了妆容。静止的时候,远远看去便如真人一般,栩栩如生。”
竹篁还在描述。
请帖上写着的地点是异珍阁,时间正是今日今时,只差一刻钟。“能和谢濯合作,异珍阁也是赚大了。谢濯这位只活在幕后的偃师,上一次在异珍阁看到他的名字,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齐同晏折起纸张收好,脚下一转,往异珍阁的方向走去,“走吧,我们也去凑凑热闹。”
一踏入异珍阁,齐同晏就被管事热情地接待到了天字号的房间。房内装饰清幽古雅,颇有一番竹墨古意,令人心境也随之变得平和宁静。
“请燕王殿下在此稍候片刻,我们异珍阁的今日活动马上开始。”
齐同晏之前也来过异珍阁,知道他们的规矩,管事的自然也不必多说什么。
不过一会儿,便有异珍阁的人站在中央的台上说话,嘴上尽是些藻饰的说辞,久久才进入正题。在前面出场的商品,虽说也是华贵不凡之物,但和后面的比终究差了点,出声的人寥寥无几,紧张的氛围感是在后面才渐渐升起的。
“殿下,你看那茶具。”
当那琅玉瓷茶具被展示出来时,齐同晏的心神微动,竹篁也出声道。
台上的人还在喋喋不休,而齐同晏已经感受到了那茶具的不可多得。“茶具只是具,但那质地温润的琅玉瓷,实在是罕见。”
没有犹豫的,台上人话音刚落,齐同晏第一个出声。
琅玉瓷自然是宝物,但大多数人一看发话的人是天字号房间的客人,一下便失了争抢的兴致。“那是天字号的人诶?”
“天字号的人,钱权势必有一样占据,而且都是大人物,我可惹不起。”
“不过只是套茶具,送他算了,我可不是为了这个来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琅玉瓷的魅力终究有限,吸引不了多数人的争抢,然而有一个少年音打破了这份低声讨论的喧嚣:“我出更高!”
齐同晏透过窗户,向四周看去,一时寻不到声音的具体来源,只能知道那个人与自己一样,都是天字号的客人。他轻轻一笑,并不当回事,继续一直加价,很快那少年的声音渐渐便微弱下去,茶具终入他手。
帖上的商品他感兴趣的不多,琅玉瓷茶具算一个,再有,就是也想见见谢濯的新作是什么样子的。都说这次的新作仿若真人,齐同晏是越发好奇了,可惜在揭开压台之物前,还有一场休息。
齐同晏舒展一下身体,斜靠在床榻上,闲闲道:“每次展示最后一个商品前,都要这样来一场休息,也不怕急死别人。”
竹篁笑道:“殿下,您也急着看谢濯的新作吗?”
“我是有些好奇,你们不是都说他这次的作品神乎其神吗?我倒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要知道十年前九妹拿到的偃甲人,可还只是个行动自如的木偶人呢,谈不上一点美观性。”
齐同晏打了个呵欠,“就是这休息时间,实在无聊,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齐同晏的话音刚落,就听耳边清晰地响起几声叩门声。
“咚咚。”
“咚咚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