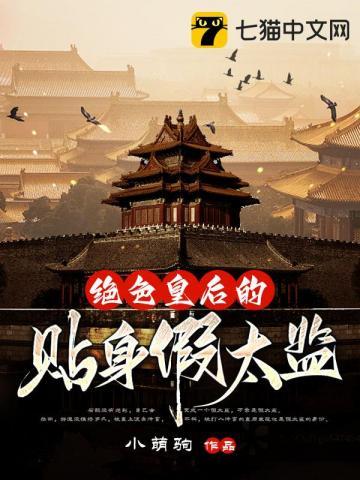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可他的尾巴会发光诶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景天想,不轻松,但人总得有些负担。
负担和盼望,才能让人燃起对明日的期待。
会变好的,会变好的。
哪怕走不到最后,至少学会不再虚度当前。
景天这样想着,忍不住把人勒得更紧。
不行。
不能放你走。
就算无法标记,留不下痕迹——
“唔……嗬!景……?!”
一阵贴合辗转豁地麻了整条脊骨,白翌在睡梦中骇然惊醒,嗑咬的刺痛叫他忍不住呜咽出声,嘴却立刻被手狠狠堵住。
喘息憋在喉咙里,连同慌乱一并让感官更为敏感。
“唔……!”
“嘘。”
背后人抵着他,沉闷的喘息声压在耳后,极小声地提醒:“别出声,孩子在你怀里。”
白翌惊慌低头,狐狸崽子嘴唇微张,贴在他的胸前,口水蹭得他睡衣湿了一大块。
这让他顿觉额头遭了重击,被捂住的嘴呼吸不顺,景天身后亮起的光像一场闪光的蓝潮,铺天浇地地将他淋湿,淹没。
当着孩子的面,干什么…干什么!
“很快……”
隔着层薄薄的布料,他完全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背后人愈渐急遽的动作。
又不是易感期,精神抽离后重聚的瞬间,连景天自己都觉得不可理喻。
景天恋恋不舍地松开捂嘴的手,手心里毫不意外地被白翌呼出的热气腾湿,正想回身抽纸去擦,怎得忽然发现手背也是湿的。
景天短暂一愣,愕地坐起身,搬过白翌的身子。
果不其然,小白蛾瞪一双困倦发红的怒眼,两行眼泪唰唰地掉。
“白……白翌……?”
白翌咬着牙,气得说不出话来,就憋着声呜呜的哭。
可把景天哭得慌了神,支支吾吾解释自己就是一时没忍住——
便觉得某个重要部位狠遭一脚重击,半边身子悬空,“咚”
地滚下了床。
疼得在地上缩成一团儿,还硬是一声没吭,怕把孩子吵醒。
再抬头,白翌已经把自己整个埋进了被子里头,就剩对儿触角怒气不消地杵得笔直。
景天连想哄人的手都不敢伸,只能茫然挠了挠下巴。
他不敢再上床了,垂头丧气地在这深秋泛凉的深更半夜,抱着白翌的长款羽绒服,悻悻缩到旁边的单人小沙发上去。
第二天一早,小洛刚跟着白翌起了床。
小狐狸没太睡醒,无精打采地坐在床头哈欠连天,一会儿一歪,景天蹲在床头,一歪一扶。
视线却是跟着一言不发、只闷头洗漱护肤,穿起衣服的白翌走。
白翌刚从浴室里出来,浴袍下露出一对细长光洁的小腿,还挂着尚未擦干的水珠。
吹风机嗡鸣着将周身轰出热气,香气更显浓郁。
略显宽大的浴袍褪到一半,就这么背对着自己坐在床沿,让景天止不住地捂嘴,强忍住大口嗅闻的冲动。
太性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