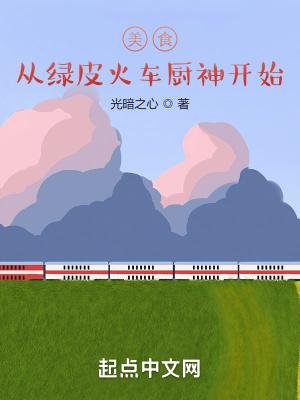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飘飘雏怎么进化 > 第154章(第2页)
第154章(第2页)
下台后,照例全组复盘,陶浸温和地提出这场的问题,陈飘飘右手在背部捉着左手的胳膊肘,仔细听讲。陶浸翻过一页纸,轻声问:“怎么到现在了还会忘记走位呢?”
“排了那么多遍,不应该有肌肉记忆了吗?”
她抿唇,在工作人员间望向陈飘飘。
气氛顿时冷凝,其他人都不敢说话,陈飘飘像回到了刚来西楼那天,陶浸当着众人的面说她没做功课。
她耳后燥热,很乖巧地低着头,小声说:“对不起,我会再好好练一下。”
“嗯。”
陶浸轻轻答,继续对下面的问题,低头安抚她一句,“快首演了,别太紧张。”
该紧张的是陶浸,当晚回去,陈飘飘口了她40分钟。
陶浸也“犯错”
了,她认真严谨、不因自己的女朋友而放松标准的样子狠狠地戳中了陈飘飘的xp,让陈飘飘忍了很久,她必须用喘息和呻吟来道歉。
之后,陈飘飘又与陶浸接吻,吻得周身都是薄雾。
尝够了,她半趴在陶浸身上,软绵绵地问:“之前你问我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那你呢?我还没问过你,这部剧排完,有下一部的计划吗?”
“下一部,没有想法。”
陶浸汗涔涔的,纤长的手托住陈飘飘的半个柔软,包裹,又放开,揉捏,又放开。
她在陈飘飘紊乱的呼吸中思考,说:“等有时间,想带你出去旅行,然后我们拍一点纪录片。”
“纪录片?”
小狐狸含着水汽的眼睛亮了。
“嗯,喜欢吗?”
陶浸呢喃着问她。
“喜欢,特别喜欢,很喜欢,很喜欢。”
陈飘飘在她身上用做梦的语气,停停顿顿地说。
喜欢陶浸带她出去看世界,更喜欢陶浸的自由。
她专注于话剧,却没有被困于话剧,她想拍纪录片,她就要去,西楼是她的一方天地,但她从来不属于西楼。
正如话剧第二幕,收尾的这两句——
“事业是我们与社会的交互。”
“我将对社会真诚而自然,我交互的事业永远忠于我自己。”
第二幕,落幕。
陶浸的床上有一个小鲸鱼玩偶,带在身边挺多年了,大学时陈飘飘曾经问她要过,陶浸说,是小马她们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要问问小马。
陈飘飘在这种问题上脸皮薄,不让陶浸去问,因此就没有属于她。
现在她早上很爱抱着这只被洗旧了的小鲸鱼,肚子上都起了毛球,手感又软又糙,但陶浸的味道被缝进了棉花里,有二十一岁的陶浸,和二十六岁的陶浸。陈飘飘后知后觉地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讨到这只小鲸鱼,它才能收集好这五年的陶浸,再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储存的气息补偿陈飘飘。
倒计时三天,陶浸接到了小马的电话。
是微信群语音,聊天记录停在几个月前,梯子回学校,说建了个新的实验楼,拍照片给她们看。
群聊头像挨个亮起来,1105全员到齐。小马的头像已经换成她家宝宝的照片,背景音里也有婴儿隐约的啼哭,她是当年最跳脱的一个,说自己就算去吃屎都不会吃生孩子的苦,然而一毕业就闪婚,一结婚就备孕的,也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