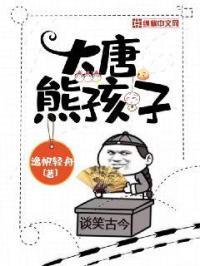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执棋者的镰刀 > 第二十二章窗(第3页)
第二十二章窗(第3页)
“解剖它。”
那柄寒光带着蛊惑向他靠近,克里德曼伸手想接,又在刚刚触碰到时触电般躲开。
少年看向仍在挣扎的兔子,久久沉默,将口中混浊的气息吐出,他似乎已经接受某种选择,匀了匀呼吸——“不。”
金属的光泽折射在眼中,那丝不该有的寒意抵在颈上,竟让他生出丝恐惧。
收回视线,少年屏息观察着那人,隔着层薄如蝉翼的皮肤,刀尖指向颈动脉——而它也像受到某种召唤,竟开始颤动,与他鲜活的生命、跳动的心脏振动同频。
“对不起,父亲?”
而与那柄抖动寒光截然相反的是表情——平稳、伪善,永远不变。
男人的眼眸垂下来,摩挲着少年的脖颈,而他看向那人眼中折出的狡黠,看着他不起波澜的眼眸,却又视若无睹,手一抽,刀放下了。
“动手。”
男人再次重申。
同时,他像似乎切断了那种藕断丝连的联系——毫不犹豫,带着麻木、顺从,克里德曼伸手接过那把刀走向属于自己的猎物。
第一刀,不过划开表皮,露出底下漂亮的红肉,鲜血顷刻涌出,克里德曼下意识想避开,但尖端沾染的温度却已凝固,他挑着眉,厌恶至极。
兔子,是端上餐桌的佳肴,而对捕食者来说对食物心存怜悯本就错误。
“父亲…”
他转而投去求助的眼神,几乎是对上的那刻,肆无忌惮将内心所想暴露,一览无余。
阿雷洛夫不作声,夺过刀,手法干脆的就将兔子开膛破肚。
纵使已低头,可仍有少许鲜血溅在了少年白净的脸上,男人倒是不避,掏出帕子擦拭自己的脸。
“兔子就是兔子,即使跑得快,跳得高,它们也只是兔子。”
上扬的嘴角昭示他的心情,哼着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刀被冲洗干净,丝绸拂去刀背的水珠,他一度怀疑对方有放弃念头——但下一秒,它调过头,那黏腻的寒光也再次锁定自己。
行为间的意思他尽然,事态本该有迎合自己的趋势,哪料刀尖向前,这回离自己又近了不少。克里德曼摸着手指,思索片刻,索性略过威胁,反手抓住刀柄接下。
“明白。”
眼神中的恶意一闪而过,他终于狠下心来,将那颗心从它体内割离,随后——
砰砰——砰砰—!
心脏有节奏的在手中跳动,克里德曼计算着次数,举着刀,被人手把手再次伸向内部——还是温热的,内部的器官多数未被摘下,而他一件接一件,像是寻找落在角落的积木,将它们从内抽离,逐一排开,整齐码列在桌面。
“它死了父亲……”
直到它成为永恒的艺术品,皮被割去卖钱,肉被分食殆尽,剩余的腐臭脏器则成了蛇的晚餐,它的生命就此定格。
它的灵魂不再哀嚎,那颗被他视若珍宝的心脏也被刺穿,像烂泥般瘫软在掌中。
铁锈味挥之不去,他看向它,看着那双红宝石似的眼眸不复那时生机。
“对不起……对不起……”
半弯的眼眸盛满泪水,一滴、两滴,落在手指上的小口处,带来刺痛,他忘不掉——那苦苦挣扎的生命归于平静。
“不要哭,眼泪会腐蚀你的美丽。”
腥臭的大手捧起少年脸颊,金色的瞳孔中折射出那人早已腐朽的微笑,对视短暂持续了一会,草药的气味又将思绪打断。
他想起来了,那人也是如此,带着那种心安的气味,会抚平伤痛,会为自己疗伤。
半晌,克里德曼才从神游状态下抽身,重新展露微笑,带着正常的情感。这次,没顾及洁癖作,他倒是大笑起来,空中还隐约留有回音。
“父亲大人。”
糖浆似的眸中水雾氤氲,克里德曼仰起头,犹豫片刻,还是伸出手——“抱…抱抱……可以吗?”
一片沉寂。阿雷洛夫依旧摩挲着那人手指上的伤口,转而,又摩挲起脖颈上的细口。
可那人接下来的行为却让他不解,克里德曼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父亲…?”
他依旧,但那种冰意回来了,连带着让他瞳孔都攸地猛缩。这才恍然大悟般抬头,可那刀刃已经完全贴在颈上,缓慢刺入。一道殷红流下,更衬肤色苍白如纸。
“父亲…父亲…!我错了…错了!求求您……!”
刚刚还神采飞扬,这会,瞳孔已经被恐惧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