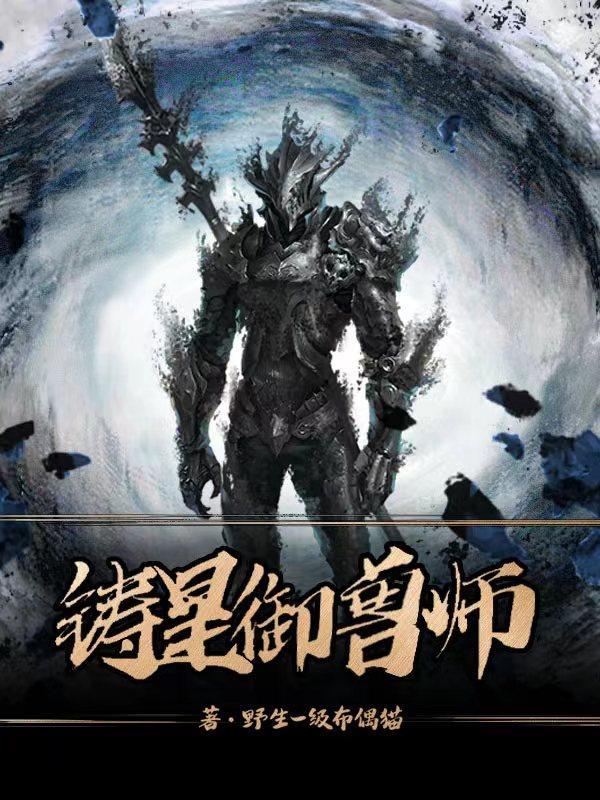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闻春声种田文 > 第14章(第1页)
第14章(第1页)
说得简单些,就是下得去死手,擦药时疼得眼前发昏也不松劲,对自己是,眼下对上姚春娘,那力道也没轻上几分。
粗糙发热的手掌按上白嫩的后腰,先轻后重地带过皮肉,痛得叫姚春娘生不出丝毫狎昵心思。
她平日看齐声做木活,猜到他手劲比一般人重些,但此时才算切身体会到他的手劲有多可怕,随随便便拿掌根往腰上一揉都痛得她打颤。
背地里偷偷哭和当着人面哭是两回事,她死死咬着唇,脸埋在枕里,眼泪打湿了枕巾,硬是忍着没叫出声来。
齐声见她不哭不叫,有些担心她痛晕过去又害怕她憋得喘不上气,他把手伸入她脖子下,将她的脸抬了起来。
一张汗湿的脸映入眼底,往日水灵灵的眼中此刻哭得发红,唇都快被她自己咬破了。
姚春娘握着他的手想推开:“你做什么?”
齐声并没多看,见她还清醒着就挪开了目光,他收回手,低声道:“别、别捂着脸。”
不拿枕头捂着,姚春娘非得哭成个傻子,她忍得好好的,齐声非把她脸露出来,她自然不听,齐声手一松她又把脸埋了回去。
但不想下一刻齐声又把她的脸抬了起来,他皱了下眉:“别、别捂。”
姚春娘本就痛得心烦,找他帮忙他还一直弄她,自暴自弃地抽泣着道:“别管我了,又捂不死我。”
齐声认真道:“能、能捂死。”
村里之前就有人醉酒后趴着睡把自己捂死了,家里人还是找他做的棺材。
姚春娘还年轻,暂时还不想死,她听见这话,迷茫问他:“真的?”
齐声点头:“真、真的。”
他说着,手底下不知揉到哪儿了,姚春娘突然哭着喊出了声,她抽抽噎噎着凶他:“你轻点啊!这是腰,不是你那一坝子硬木头!”
齐声被吼了一句也没生气:“轻、轻了好……”
姚春娘的眼泪断线珍珠似的往下流,哭着道:“轻了好你就轻点啊。”
齐声抿唇看了她一眼,结结巴巴接上后半句话:“好、好不了。”
虽是这么说,但齐声揉着手下细软的腰身,总感觉如果再大点力气,姚春娘的腰就会断掉。
他又倒了几滴药酒在手上,盯着地面手掌摸索着继续在她腰上来回揉按,直到将她后腰都揉搓得发热发红,才松开手。
齐声拉下她的衣摆,迅速起身背过脸,拿起床头木柜上的瓶塞塞回瓶口:“好、好了。”
这药效果好得离奇,姚春娘此刻后腰火烧似的热,的确没那么疼了。她擦了擦泪,像是把他当成了村里的老医生,瓮声瓮气地问他:“这要多久才能好啊?”
齐声道:“十、十来天。”
姚春娘苦巴巴地闭上了眼:“那我十天都不能下床吗?”
齐声摇了摇头:“痊愈十、十多天,下、下床两三、三天。”
姚春娘“哦”
了一声,她抬头看着他宽阔的背影,问他:“那你明天能再帮我上一次药吗?”
她像是一时犯懵,不清楚叫他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来她屋内意味着什么,齐声这样想着,把药酒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好半晌才轻轻点了下头:“可、可以。”
不料姚春娘心里明镜似的清楚,她有气无力地趴在床上,提醒道:“不要让人看见了,会说闲话的。”
齐声:“……嗯。”
决心
姚春娘养伤养得憔悴,齐声帮她擦了两天的药,她躺了足足三天才下床。
她如今当真是废物一个,什么粗重活都沾不得。闲得无事,趁空便把约好给糖店何老板的小竹篮做了。
之后在家里又躺了两天,姚春娘收到了她爹娘托人捎来的信。
她爹娘不识字,信是由人代笔,写的时候估计着想到哪便说到了哪儿,交代了一大堆杂七杂八、摸不到头绪的琐事,姚春娘看了大半页纸才从字里行间找到那句不起眼的“家里一切安好”
。
她家无恙,亲戚家却遭了难。信里说地动时她三叔三婶带着小儿子在家里午睡,没来得及跑,房子震垮了,一家老小全埋在断裂的梁下。
孩子没事,但她三叔三婶却因为把孩子护在身下伤得不轻,等邻居把人从废墟里刨出来时,三婶已经没了气,如今留下她三叔瘫在床上半死不活地吊着半条命,由姚春娘的爹娘和大叔大婶照看着。
两位已经出嫁的女儿听说这噩耗全都匆匆忙忙赶回了家,成日守在床边哭得不行,但将死之人回天乏术,两家人已经在悄悄准备后事。
姚春娘读完信后唏嘘不已,但却也并不多痛心。
自她记事起,她家和她三叔三婶家就不和,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又因为赡养老人的事儿闹得越发厉害。
老人多病,要钱吃药,要人看顾。这家嫌那家没出钱,那家怨这家没出力,一个姓生生吵得像几辈子的仇,如今一个村的人都知道他家几兄弟不和。
姚春娘的爷爷奶奶走后,她三叔三婶夜里得了闲,又生出个儿子,从此之后更是趾高气扬,常常拿她娘一辈子就一个女儿这档子事来气她娘,什么恶毒话都说得出口。
姚春娘撞见过几次两人吵架,本来长辈吵架晚辈不应该搭话,但姚春娘实在听不下去,她娘在后边骂,她抄起扫帚就去赶人,彪悍得很。
姚春娘嫁来梨水村后,还担心过她娘会不会吵不过她三婶。
如今听说人没了,一时觉得世事难料,一边又坏心眼地觉得开心,起码从此后少了个人找她娘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