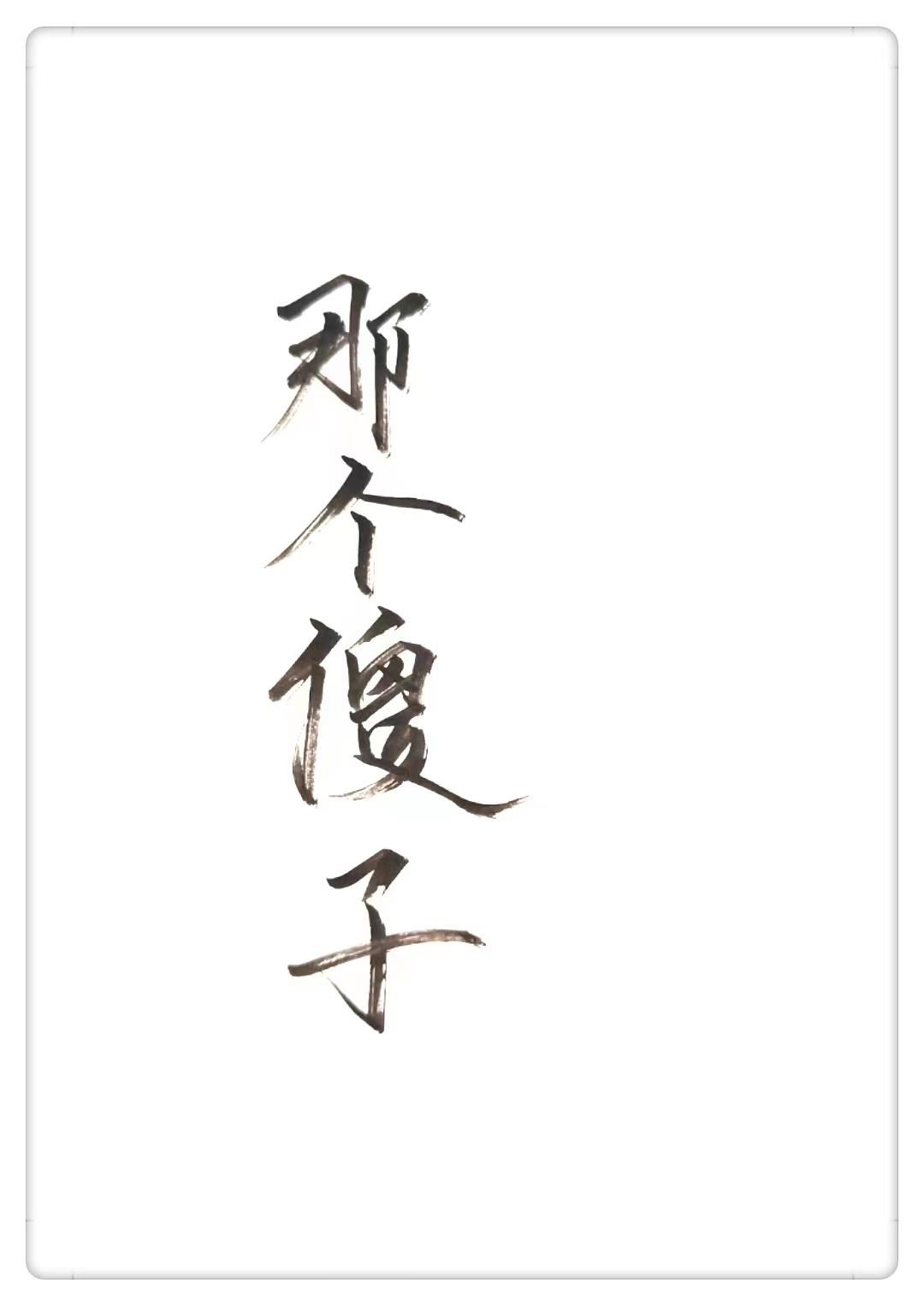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成为他母后 > 第54章(第1页)
第54章(第1页)
引人情不自禁走向她。
或是当真察觉到她喘气不能,杨恭松开,将额头抵在她额间,沙哑道:“缓一缓,嗯~”
他的热气,他的心跳,尽数将小娘子包裹,不留下一丝空隙。她像是一条鱼,被大浪拍打,艰难出声,“嗯,我想歇一歇,太累了。心跳的厉害,我怕是要死了。”
杨恭急促一声轻笑,那气息一径朝耳朵里头钻,令崔冬梅浑身颤抖,一股奇异无比的感觉涌上来,一时之间热泪盈眶。
“你笑话我。”
说着,像是没脸见人,更像是控制不住自己,任凭泪珠在眼眶中打转,自己则一个劲儿朝男子怀中钻,藏在他衣襟之下。
那滚烫泪珠,就此落到男子胸前,他腾出一只手,抱着崔冬梅后脑,紧紧靠着,“歇歇就歇歇,崔二娘子说一不二,我都听你的。”
听他如此说道,分明是将她的泪水当了真,崔冬梅一时庆幸,一时按耐不住。
学着他适才模样,不停地喘气。借衣襟遮挡,借身姿阻拦,她刻意呼出的热气,在半开的衣襟之间来来回回,窜来窜去,惹得杨恭登时大步朝前,一个劲儿将她放在卧榻之上。
男子一手抚住她肩膀,一手无可安放,直勾勾盯着小娘子看。
崔冬梅做了错事,闹了一场,正欢喜得意,毫不客气地抬起下颌回视,笑脸盈盈,眉眼微挑。
好似在说:二哥哥,我做怪了,你能将我如何。
他委实不能如何,舍不得打,舍不得骂,连她似有似无的泪水,也舍不得。
“精怪的小丫头,往后有你好日子过!”
崔冬梅得胜,喜不自胜,那微微上抬的下颌,挑得更厉害,半眯着眼,如同张扬傲气的小貍奴。
“往后是往后,今儿个,二哥哥答应我了,让我歇歇。天子一言,绝无反悔。”
杨恭憋屈得厉害,“我是说过让你歇歇,可没说让你什么时候歇歇。”
崔冬梅连忙脱下鞋袜,朝卧榻内侧走去,还将被褥等物件挪到中间,作为隔档。口中念念有词,生怕杨恭反悔,“歇歇,自然好生歇歇。”
这话,说得是极为害怕再有个什么。
男子立在床榻之侧,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她动作。过了半晌,“今夜还未盥漱。”
崔冬梅:忘了诶。
他抿唇一笑,“你先歇着,我沐浴后再来。”
小娘子点头如蒜,“嗯,你去,赶紧去。”
正阳宫浴房,和西侧间就寝之地,相隔不远。杨恭的脚步远去之后,崔冬梅半躺,脑子混沌得厉害,胡乱想着,丝毫没有头绪。夜深人静,隐隐能听闻从浴房传来的动静。初次听闻,并不真切,时断时续。可后来,像是有个厉害法器,将那响动放大,再精准无比传到她耳中。
淅淅沥沥是水声,窸窸窣窣是衣衫翻动之声,那碧波荡漾,来来去去,又是个什么声响呢?
不知为何,今夜陛下沐浴,较之往常慢了许多,崔冬梅等得有些不耐,迷迷糊糊睡去之际,还能听闻阑风长雨之声。
睡意朦胧之中,她恍惚听见有人在喊她,似有甚无比着急之事。崔冬梅迷迷瞪瞪睁眼,“娘娘,太后不好了。陛下已经起来了。”
“什么?”
崔冬梅糊涂得很。
“别吵,让她睡吧,我去看也是一样。”
杨恭的话,不知从何处传来。
崔冬梅听罢,真想继续蒙头大睡,可适才的话,像是有谁不好了?
“谁不好了?”
“太后,宁安殿叫了太医。”
崔冬梅一个激灵起身,“快快快,更衣更衣。”
匆匆忙忙之间,崔冬梅一股脑将这些时日之事,连带着从前和太后的约定,一齐告知陛下。话说那日立政殿不好,消息传到崔冬梅口中,再由她吩咐隐瞒不欲太后知晓,已然迟了不少。事后,崔冬梅亲自前往宁安殿请罪,说都是自己的错,不该如此。
然而,太后却似了却心事一般,笑得开怀,说陛下的从前,那是一头倔驴,不愿意的事儿,谁来强迫也没有用。他愿意喝,补坏了也愿意,那是他自己的心向着你。若是个旁人,你看他如何收拾。
彼时,崔冬梅听得满眼酸楚。她知道,太后口中的旁人,说的是他自己。
母子仇怨,她答应帮助太后,但无能为力。食言而肥,着实不该。
而今再闻宁安殿传太医,崔冬梅思索着将这一些告知。
她想,愿意不愿意,原谅不原谅,都不是她能左右。二哥哥若是愿意抛却往事,那最好不过。二哥哥若是不愿,食言而肥的后果,她崔冬梅自己承担。
及至他们二人收拾好,入到宁安殿,里里外外宫娥跪了一地。崔冬梅暗道不好,看向陛下背影,见他甚异常也无,不禁揪心起来,无声朝他靠过去,一齐转过屏风。
卧榻上的太后,饶是崔冬梅日日得见,也不免惊呼,一瞬间老得可怕。
她皱巴巴的面皮,耷拉在眉骨之上,眼角些许皱纹,更显疲累沧桑。抹额宽大,其上繁复绣文,是这卧榻之上唯一一抹亮色。
崔冬梅情不自禁出声,“太后。”
太后虚弱一笑,“崔二,你哭个什么,人总有一死,不是今日便是明日。繁华富贵,到头来也都是去见阎王。”
话说得豁达,可崔冬梅知道,她心中仍有念想,仍有遗憾。太后说话间的眼神,一直盯着陛下看,小心翼翼,却又光明正大。小心翼翼者,是双眸中期盼,正大光明者,是当下众人对此无不知晓。
崔冬梅:“太后想必有话和陛下说,我还是出去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