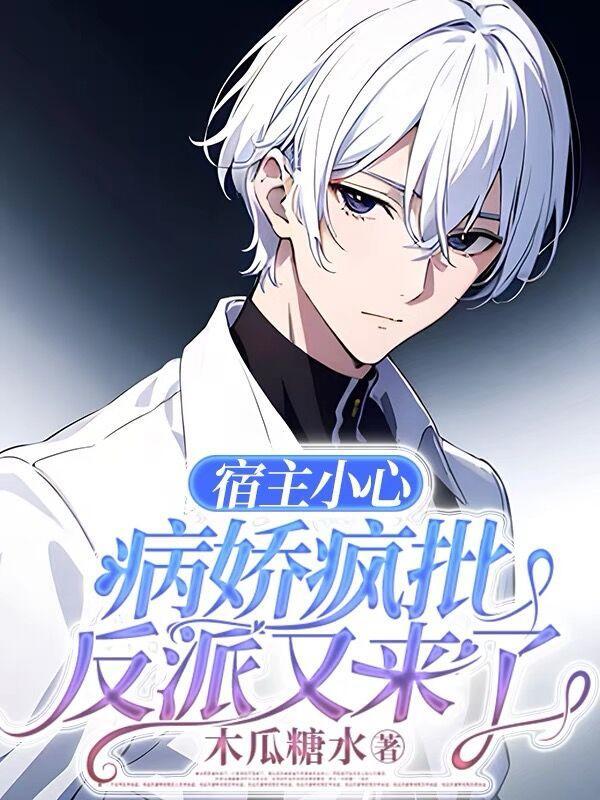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欢喜娇娘伏寒程宝缨 > 第48頁(第1页)
第48頁(第1页)
再說,符清羽會為了她和楊家翻臉嗎?
寶纓真的不確定。
文竹見她臉色慘白,顯然是嚇到了,急忙安慰說:「我只是提醒你多注意,其實不大可能發生……唉,說來說去,癥結還是在陛下那裡。他不臨幸你,就把人這麼晾著,整天和低級宮女一樣拋頭露面的,怎麼擋得住狂蜂亂碟?」
寶纓默默垂下了眼。
曾經她天真的以為,無論皇帝是否臨幸她,只要有太皇太后那句話,她至少能在宮檐下苟活一生。
可是,太皇太后畢竟去了,人走茶涼,那句話在多大意義上算數,誰也說不準。對方又是楊府的大公子……
楊會輕浮霸道,寶纓自是不喜,而楊府,更是讓她深深恐懼。
雖然她對朝堂上的腥風血雨了解不多,但當初父親出事,正是楊用和兒子楊平力主給父親定罪,以近乎於斬草除根的態度,將程家連根拔起。
這樣深的芥蒂,就算不管內心的朦朧的愛意,就算她可以任命當楊會的妾室,楊府其他人會放過她嗎?
真進了楊府,她要怎麼活?
安分守己,不爭不搶,原來也並不能躲開麻煩。那一刻,寶纓深刻意識到,自己是如此卑微和無奈。
她下意識想要求助的人,或者說唯一能夠抓住的人,只有符清羽。
要是陛下臨幸她就好了……那些慫恿她勾引皇帝的人,他們說過的話在耳邊縈繞,寶纓暗暗打定了主意。
不成功便成仁罷。
反正符清羽再怎麼惱她,罰她,鄙夷她,都不可能比被楊會強占更壞了。
像刀子懸在頭頂,寶纓心神不寧,她想儘早試試。
只是連她也沒想到,機會來得那樣快。
……
那是個頂寒冷的冬夜,剛好輪著寶纓前半宿守夜。
符清羽對聲音極其敏感,喜靜,不喜人近身,也不喜歡被窺探。守夜的人睡在外間,隔著重重幕簾,只聞其聲不見人影。
寶纓懷著不可告人的心思,明知內室的龍涎香快燃盡了,卻拖著沒去換。心裡想著,若香燃盡前符清羽便歇下了,那她就借著換香的由頭,進到內室,和他獨處。
符清羽那天飲了酒,平素白淨的面龐湛出酡紅,像白玉染上了紅髓。
一貫清冷的眼也少見的帶著幾分迷茫,卻還是依照慣例,帶了一沓摺子,梳洗後就著琉璃燈的光華批閱。
映在牆上的影子,照舊運筆如飛。
卻終究是肉體凡胎,批著批著,氣息趨於紊亂。又過了不久,符清羽叫人拿走奏摺,熄燈躺下了。
寶纓留守在外面的小榻上,豎起耳朵,極其罕見地,聽到符清羽在踏上不住翻身,呼吸沉滯。
他沒睡著,所以寶纓悄悄起了身,手腳卻因緊張而變得冰冷。
她在門邊輕聲問:「陛下,香快燃盡了。您要是還沒睡,奴婢現在換了?」
裡面,符清羽深重地嘆了口氣,似乎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調用起特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