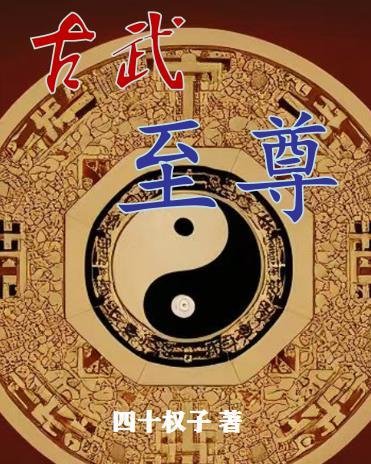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1987我的导演时代魏不弃 > 第十二章出发(第2页)
第十二章出发(第2页)
江衫吸了口气,脸一摆,懒得理睬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货。
时寻也不计较,
坐飞机,出国,对他来说,也是平生头一遭。
头也不回,乐呵呵自顾自去朝前走。
也不说帮姑娘拿一下行李。
还得是王智汶,都不用开口,主动就凑过去帮忙。
对比某人显得的就贼绅士!
不开玩笑,这年头,坐飞机真是个高档行为。
那都得是有背景有身份的主,才舍得。
据说,乘客还能免费喝上茅台。
换后世碰到某些乘务员,不给你橙汁就不错了。
你要会说‘洋文’,那另当别论。
真坐上了吧,时寻感觉也就那样。
旁边俩新鲜劲倒是长点,满是好奇的打量着周遭。
尤其某个大脸猫,更是死乞白赖的要跟王智汶换座,坐窗户那块。
得亏是不能开窗,否则非得把头钻出去,好好呼吸一下才算过瘾。
不过,很快,她也疲了。
路线是耗时最长的那一班。
五十一个小时的飞机。
她还晕机。
直接人坐麻了。
哗啦啦的吐。
总算,到了不拉登顿机场。
距离目的地,还有四十公里。
好幸有人接。
二十八日当晚,总算下榻了酒店。
一路上,也主要是时寻在跟接待的人交流。
那两货,英文也会,但都是哑巴英语。
听倒是大差不差,说就一股塑料味了。
“哎,你英文怎么学的?”
“我从小看外语片学,都没你说的这么好。”
江衫父亲是北影厂的,自小没少看内部片,一直觉得自我感觉良好,但真见到老外,对方说快了,自己却反应不过来。
“买本字典,背单词,然后听外国台的广播。”
“就这?”
江衫很受打击。
“不然呢?”
“……”
话说,八十年代从国内那个环境,来到金碧辉煌,散艺术和人文色彩的国外酒店房间。
三人都感受到了浓浓的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的洗礼。
怎么还有人酒店房间放饮料让人随便喝的呀。
自助餐,游泳池,健身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