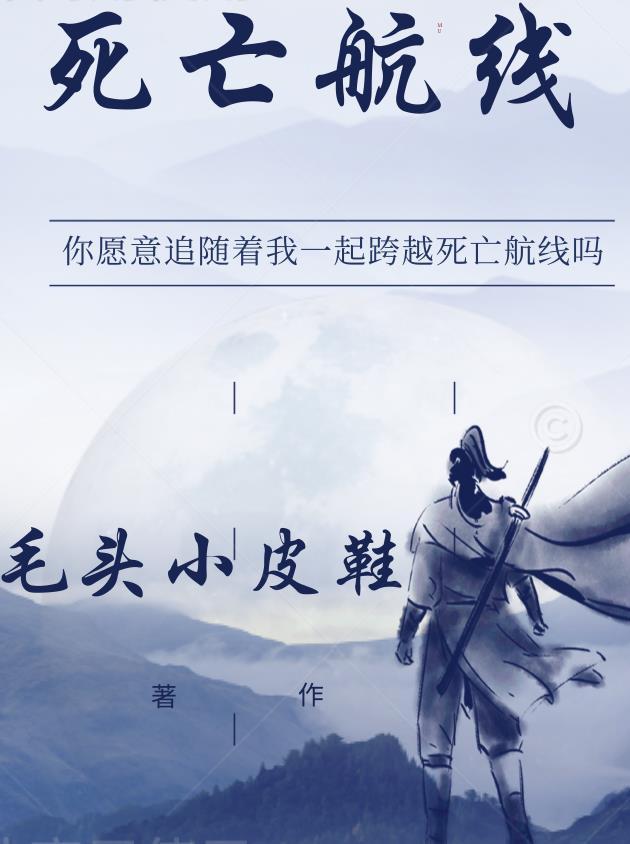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替嫁风云宋晚的结局 > 第14章(第1页)
第14章(第1页)
苏锦听的面色一窘,脸上的两抹绯红瞬间蔓延到了耳朵根下。
隶王妃忍不住用手帕掩住嘴角低声地笑了起来。
“休得胡言!”
娴妃见状,急忙打断了长公主的问话。
“哪有这样说自己弟弟的?看看你自己还有没有一点公主的样子?一个女儿家什么荤话都往出口说!”
长公主一向不拿母亲的训话当回事的,当下便回道:“我已嫁做人妇,男女那些事有什么可遮掩的。何况弟妹又不是少不更事的小孩子,若是他们俩人之间为了这事起了隔阂,母妃为着姨母泉下有知,少不得又要费些脑筋。何不早日问个清楚?”
娴妃被女儿的一番话堵地不知所以。
此时,隶王妃插话道:“长姐说的在理,姨母的临终遗言一直是母妃的心病。这么多年了,可不就是眼巴巴等着老四娶妻生子,这下娶妻算是落定尘埃了,只等着生子了。这等大事,可马虎不得。咱们还是听弟妹好好说一说个中缘由再做定夺。”
娴妃觉得有道理,一时,母女三人齐齐望着苏锦,等她的确定答复。
苏锦听她们言语了半天,早就羞窘地不知所以,她哪里想得到,大成的皇室公主和妃子们,竟是这般“豪放”
。
看她们这个样子,似乎很紧张睿王赵言的身体。
苏锦稳了下心神,才故作委屈地说:“不怪殿下,都是我不好,大抵是我蒲柳之姿不合殿下的心意,所以才被冷落至此。”
说罢,苏锦佯装伤心,捻起袖口往眼下按去。
长公主轻轻拍着苏锦的背,事情不是她想的那么夸张,不免有些失望。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来有之。只是再怎么样,也不该这样对待新婚的妻子。这个老四,该好好安顿才是。”
长公主虽然没有被满足刺探别人隐私的好奇心,但是当下也不得不生出一些可怜心。
娴妃悄悄舒了一口气,待苏锦情绪稍微缓和,才说:“你远道而来,不了解言儿的性子,他不是那般不讲道德的人。无论如何,你们再相处一段时日,好歹——先有了夫妻之实,相处久了感情慢慢也就生出来了。男人都是一个样子,你不要太过于灰心了。”
苏锦听着,在心里暗暗回道:谁要和他有夫妻之实?这感情谁爱要谁要吧。她等不及三月之期就想离开这是非之地了。
“那么,还请娘娘在太后跟前好好替我说个情,毕竟这事儿,也不是我自个儿能做得了主的。”
苏锦仍是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令娴妃三人看了不免又心生一丝不忍。娴妃点头道:“这是自然的。如今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也不用这么客气。有事只管来和我讲就是了。”
隶王妃也关切道:“是了,你生的这样一副好相貌,若是在这京城里,准是世家大户抢着求娶的。睿王再怎样,也绝不会因为你的外貌冷落于你。待回头,我让隶王殿下好好问问他,兴许是有别的事也未可知。”
隶王殿下?
苏锦暗暗叹气:这傻女人,竟是什么也不知道。她若是知道自己是隶王殿下安插在赵言身边的探子,估计会后悔管这烂摊子的事吧。
“皇嫂还是别对隶王殿下说了吧,毕竟,这等私密之事,越多的人知道,只怕睿王会不高兴的。”
隶王妃见苏锦婉言拒绝,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连连答应。
正说着,有宫人来传话,说睿王与皇帝议事完毕,晌午要在尚熙殿摆家宴。
“哦,看来午饭要在皇后那里吃了。既是家宴,隶王殿下也该到了吧?”
听娴妃问话,那宫人回道:“给隶王殿下通传了。凡是在京的王爷公主都得了陛下的口谕,一一通传下去了。”
听那宫人如此说,长公主转了转眼珠子,才问:“想必太子殿下也能出来了吧?”
“公主猜的没错儿。陛下一早就让人解了太子殿下的门禁,这会儿已经在东宫了。”
那宫人说着脸上已带了两分喜色,不必说,定是皇后身边的人了。
长公主忍不住翻个白眼:真是个狗仗人势的东西!
打发了送话的宫人,娴妃便命人给苏锦和长公主、隶王妃理了理仪容。
娴妃最是注重仪容的人,虽年岁上了一些,眼角也有些细纹,可是穿着打扮却是一丝不茍,宫里负责梳妆打扮的宫女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的。
看着长公主略有怒色的面容,娴妃只好拉着这个唯一的女儿,语重心长地安慰道:“你如今都是当了母亲的人了,说话不可再一味地图自己快意。你再不喜欢太子,他也是大成的储君,未来的陛下。何苦为了一时快活,不为孩子好好打算呢?”
听到这里,长公主不免悲从心来。
“我的第一个孩子,便是无故糟了东宫的毒手才没了。母亲是知道的,我没有招他惹他,他竟为了区区侍妾对我的孩子下毒手。这口气,要我如何忍地下去?”
说着,她的眼泪已经大颗大颗地滚了下来。
“私铸钱币这么大的事,上上下下倒台了多少官员,他倒没什么事。我原以为······原以为······”
长公主终于控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我以为老天终于开眼了······母亲亲眼看见的,我那可怜的孩子,他都已经是个成形的胎儿了!我的心好疼啊母亲!”
苏锦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被长公主的哭声震撼地久久不能回神。适才还谈笑自如的女子,在听到太子的消息,突然崩溃大哭起来,令她心里也升起了几分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