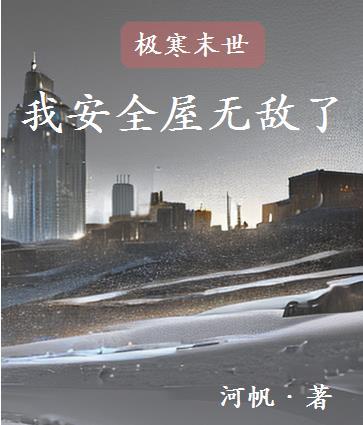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春回冰解水十三讲的是什么 > 第12章(第1页)
第12章(第1页)
萧笙并不想惹事,隔着老远便退开,贴着街角侧身站好,以免被这不长眼的疯子撞伤。
可他白得太耀眼。马上的疯子惊鸿一瞥间,被路边的美男子吸引了注意力,他突然勒马!
骏马前蹄离地,引头嘶鸣,在萧笙面前激起一片尘土飞扬。
尘土散去,两人四目相对。萧笙微微抬头,眉头间有一道若隐若现的沟壑,竭力克制的怒意只在此处有略微的呈现,眼睛和表情仍是冷的。
马上的人猿背蜂腰,和他的马儿一样精壮强健,结实的肌肉在薄衫下呼之欲出。他年纪比萧笙大些,一张脸说不上英俊,因一抹狂傲不羁的笑而别有风情,但不可一世的模样又着实招人厌。他扫过萧笙腰间的佩剑,以为那又是富家公子哥的装饰,便伸出马鞭勾起他精致的下巴,轻佻道:“好个冰山美人,这是哪家的小公子?”
萧笙面色沉静,脑中却已天雷滚滚。
我堂堂浮屠宫少主,无影剑传人,江湖中人人闻风丧胆的魔头,居然当街被一个大老爷们调戏了!
他眼中杀意一闪,又想起萧艳殊的叮嘱,惊觉犯不着为个登徒子去受寒毒之苦。于是不忿的扭头,将那恼人的马鞭错开。
林桓上前一步,挡住萧笙面前,冷声道:“休得对我家公子无礼!”
“嚯,”
那登徒子轻哂道:“出门也不带条好狗,这老狗还有力气咬人不成?”
他出言不逊,林桓二话不说拔剑。空气中寒光一闪,登徒子还未看清,手上的马鞭已经被斩断,仅剩短短一截杆子握在掌心,断口紧贴着虎口,整整齐齐没有一丝毛躁,刀工堪比御膳房的大厨。若那一剑再多削一点,非把他半个手掌削下来不可。
登徒子脸上的笑容渐渐凝滞,目光从萧笙的脸挪到林桓昏黄的老眼上,冷声道:“没想到还是个练家子。这年头,用剑的人可不多了。”
林桓的剑已经回鞘。两边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登徒子只道:“在下还有事在身,来日再来讨教。”
便策马离去。
临走,他阴鸷的目光在萧笙身上流连,暗道:狗都如此厉害,主人想来也不简单。
他舔了舔嘴唇,萧笙那张俊美的脸在面前挥之不去,唤起他的兽性,真是叫人欲罢不能。
洪府的人已经听到风声,全家赶着在天黑前出城,连金银细软都不要了。
洪老爷早些年不信洪,他凭一套双截棍法行走江湖时,用的还是“徐颇”
这个名字。
二十年前的北上之行,奠定了他一生的悲剧。这两年旧友惨遭灭门的噩耗不断,他早已如惊弓之鸟,连父母给的姓名都抛却,解散门派,只带着亲人和亲随寥寥数人躲到泉州来,一心只想茍且偷生。
不想,浮屠宫的人还是追来了。
洪府的人正在摸黑跋涉,密林中传来一声尖锐的哨响,惊得树上栖息的鸟雀齐飞,气氛惊悚非凡。
徐颇只觉得自己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张臂拦住身后的眷属,问道:“来者可是浮屠宫的萧公子?”
黑暗里传来一个声音:“不是。”
徐颇顿觉松了口气,毕竟天下没有什么事情能惨过灭门。
那鬼魅的声音再度传来,道:“我是特地赶在萧公子前,来找徐门主讨个东西,顺便……送你们上西天!”
徐颇心头一寒,想起身后的一家老小,强做镇定道:“要什么东西都好说,我给你就是了。何必取人性命。”
“徐门主二十年来将那东西藏得这般好,”
一个高大的人影从夜色中走出,脸上竟还挂着笑:“若我手脚不干净,传出点什么风声,那天下人明天不就都来追杀我了?”
徐颇借着星光看清他的脸,惊愕道:“是你……你是五毒教的人!”
正是五毒教当年在关外截杀六门派,抢走半本叶虚经。
“徐门主好记性!”
来人竟鼓起掌来,清脆的掌声在林中回荡,久久不绝:“二十年前,我荣瑟不过是教主身侧的一个小厮,徐门主竟记得住我的脸,不愧是能成事的人!”
他是荣瑟!
江湖中传唱了几十年“一僧一道双刀笑”
,这十几年,却有人给出了下联:“鬼道五门逆天行”
。说的正是包括荣瑟在内的几个魔头。
当年五毒教因叶虚经起了内讧,继而分崩离析,几年混战之后,重新形成五派割据的局面,分别以蛊、蛇、音、暗器、毒见长,荣瑟正是其中一派的头领,特长是暗器。虽然同是五毒教的脉系,五派却互相不对付,不时殴斗,殃及池鱼,搅得武林不得安宁。
世人只知道五毒教分崩离析,却不了解他们得了叶虚经的内情。徐颇心思转圜一周,心道这五个后起之秀之所以能称霸武林,又势均力敌,不分伯仲,定是各自抓了部分叶虚经在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斟酌着开口道:“荣门主也是当年之事的见证人,东西早已给了你们。你要找的东西,恐怕还得去找你旧时的朋友讨。”
“哈哈哈!”
荣瑟仰天大笑,笑够了才厉色道:“叶虚经在谁手上我当然门清!可若徐门主说东西全给了五毒教,可就不太厚道了!”
“叶虚经是你亲手交给老教主不假!”
荣瑟迈步走来,步步紧逼:“可我想问一句,那半本经书的封底去哪了?”
“封底……”
徐颇艰难自持,苍白辩解道:“一张封底有什么要紧的,当年兵荒马乱,许是在打斗中弄丢了。”
“没什么要紧的玩意,也值得徐门主藏二十年?”
荣瑟已经走到徐颇面前,狭长的眼睛闪烁出杀意。他一把掐住徐颇的脖子,逼问道:“说!你把那页纸藏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