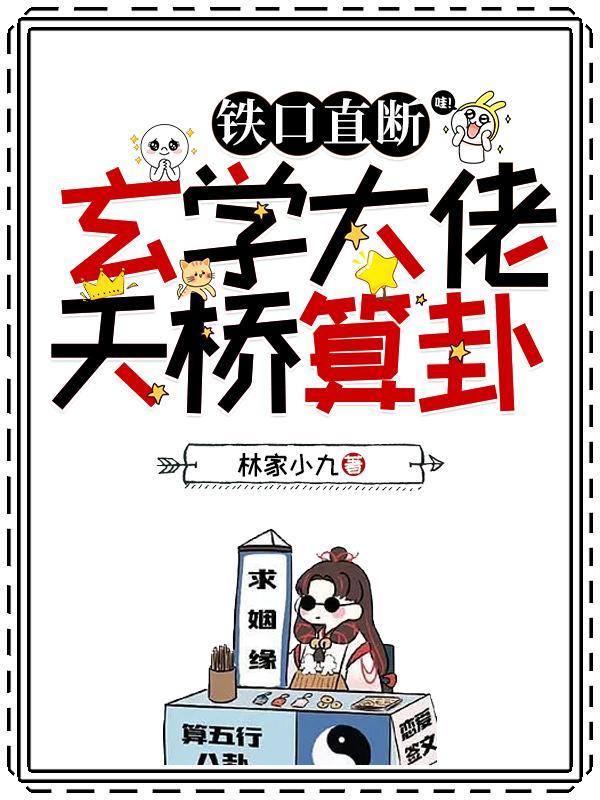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对于侠的定义 > 6 章(第1页)
6 章(第1页)
里的?说着,放她进来。
明彩满身血迹,肩上还有一道极深的刀伤。她从台上跳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有个模样很秀气的侍女,告诉我你在这里。」
我叹息,又摇头:「我问的是门前的侍卫,你是怎么进躲过他们的?」
她漫不经心地答:「我说我是御用画师,要进来逛逛。他们非不听。我只好跳上屋顶,没想到屋顶上还有三个带刀的,让我放倒了。」
她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终究是放心不下。我右手轻点了她锁骨、右肩、右肘,说道:「砍伤、刺伤两处。骨损一处,筋损两处,右臂差点断掉。再严重些,我便也修不好你。即便现在这样,修好你也要一个时辰。」
明彩站不稳,只得靠在墙上,她从腰间抽出几排画卷:「我没事,我是来给你带几幅画的。」
我只轻瞥了两眼,有轿子、椅子、花瓶。都是些宫中普通的物件。
但细瞧才觉得有异。
「等下,明彩,这都是你画的?」
「当然。」她的声音有点干瘪。
「你什么时候把死物画得这么好了?」
她没回答,我这才发觉明彩面色惨白,嘴唇青紫,倒在了墙角。<olstart="12"><li><li><ol>
天色渐晚,日光昏黄。
她伤得比我想的还重,甚至痛及筋骨,脏器也有轻微的淤血。我花了足有三个时辰才修好她。最后实在太过疲倦,我直接倒在床头睡去。
我梦见明彩,见到的是一片雪白,白色的柳叶从我面前像素湍一样飞过。我听见明彩在我身旁清唱,唱的是我没听过的曲调。那唱腔如泣语,却又带着几分洒脱。她的声音简单真挚,一字一句唱道:
自有智,自有惑,辨得物与我。
百种阳,百种阴,化作天地和。
不见善,不见恶,唯留因和果。
千般圣,千般魔,任由他人说。
这曲是什么?词又是什么呢?
到最后,我满脑子回荡的都是最后那句「千般圣,千般魔,任由他人说」。沉醉之间,却已醒来。
我醒来时,明彩就坐在床边。其实我是很想问那天分别之后她为什么要哭的,更想追问那梦中的曲调。但我终究没有问出口。
她先开口问:「你身子,还撑得住么?」
我说:「我当然撑得住,这都是末事。我给你讲件大事,希望你不要怪我。」
她说:「你说说看,我也先听听看。」
我指着柜子说:「侍卫被打伤,宫里严加戒备,我这里也被搜查。为了把你藏到柜子里,我当时把你拆了。」
「拆了?」
「就是拆成若干块,成一摞,然后堆起来。虽然不告诉你你也未必知道,但我还是觉得不该瞒你,况且……」
她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明彩浑身上下摸了摸,然后指着我,我连忙示意她小些声响。
「你摸了我全身!」
我没想到她竟然着眼在这点上,哭笑不得:「这倒是其次,只是我单单觉得把人四分五裂,有违天理。而且不是还隔着衣物么……」
「我倒觉得蛮有趣的。」
「这可不是什么趣事啊,明彩。」我摇头道,「父亲曾说人匠里有先人为了避难,自己拆分了血肉筋骨藏匿起来。虽然最后被他人恢复,却受不得被拆解后那种状态,终日恍惚,郁郁而终。」
她显然没能听进去我的说辞。
我拿起那画卷问:「那接着说点大事。这些画,到底是什么来由?」
「的确是我画的,是我当上宫廷画师后,所画的一些宫中物件。」
「但你根本不会画死物啊。」
她跳下床,然后笑着道:「所以那些都是活物啊。」
我不禁悚然。
「你是说,这些曾经都是人?」我问。
「是人,而且他们现在还活着。」
「这不太可能,如果把物件镂空,以人匠的技法把人切分软化,将之注入,或者为人蜕皮,置入某个物件里,让血脉经络和外物长在一起,这两种难度都很大,而且就算能成,这人也活不了多少时日。」
「那你看这张。」明彩从袖中抽出一张褶皱的宣纸,上面潦草地画着一个人形。是我那夜里化进伞的老者。
我问:「你也见过这老者?」
她说:「在夜里曾见过一面。时间太短,只画了个大概。我拿这纸问过一个侍女,她说这老人要去当『椅子』,只是体质太差没当成,成了所谓的『废人』。」
我半晌无语。到底是怎样的人,要将人抽成模子,做成椅子,弄得分崩离析,生不如死?要这样违天理,逆人伦?这宫里我见过的人事有多少,未能的认识又有多少?我触到的恶可能只是河川,未见的恶也许是汪洋大泽。
心口有一团火在灼着,烫得难受。
我凝思了片刻问:「你一直说的侍女,是不是叫温良?」
明彩摇头说:「不知。我当了画师后,是那侍女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