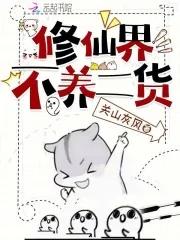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鹤梦疑重续可以形容什么 > 第53章(第1页)
第53章(第1页)
为首的一人提刀挡开,第二人、第三人一拥而上,一人攻左一人攻右,明显是经常训练配合,远非一般人可敌。好在阿琢轻功不错,身形灵活,左右腾挪,三个人一时竟拿不住她。
正在纠缠之间,其中一人忽然“咦”
了一声,此时月亮从云层里探了出来,能清楚地看到阿琢脖子上挂着的玉牌,半扇鱼龙呼之欲出。
几个人一齐收了手,站在原地面面相觑,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犹豫了半天,为首的那个人道:“请问阁下是否是来找人的?”
阿琢直接问:“他在哪里?”
几个人明显松了口气,为首的那个抱拳道:“不知是客,多有冒犯,请跟我来吧。”
阿琢也不知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陷阱,身形未动,几人见她犹豫,卷起手腕露出手肘处的鱼龙纹身:“请贵客放心,我们几个都是公子身边人,断不会害您!”
阿琢一直到看到他们的纹身才反应过来,这些人居然是章氏的士兵!云州怎么会有章家军?
武卫营
她有点惊疑,也只能表面上保持镇定,随他们进入庄园。一直走到尽头的正房,推门进去,屋里并没有灯光,那几个人都没有跟进来。
她借着月色观察了房间,并不像是关押犯人的地方。看了向晓并不在这里,要不要立刻离开?正在犹豫间,却听到身后传来关门的声音。
阿琢怀里还有一只匕首,她咬了咬牙,抽出匕首反手回刺,来人出拳格挡,阿琢借势转身,匕首在空中划过一道寒光,直逼对方咽喉。来人身形后退,堪堪躲过这致命一击。
阿琢剑锋凌厉,刀刀带有破空之声。来人却只是闪躲,并不还手。
电光火石之间两人已经过了数十招,阿琢看对方并不还手,收剑停下了攻势,那人这才戏谑道:“跟你见面当真凶险,一着不慎,命都得搭进去。”
随着他从暗处走出来,阿琢才看清了他的容貌:“章恪?你怎么会在这里?”
那夜之后,那一千章家军和章恪就都凭空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司马协上表,把责任都推到章恪身上,太子也不置可否,没有任何惩处或是勉励,当真做实了仁慈天子那一套。
章恪走到桌边点上油灯:“这话该我问你,你怎么到这来了?”
“我的护卫在庄外走失了,我进来寻找。”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明日我叫人送你回建安。至于你的护卫,暂时不能走。等时机成熟,我自然会放他回去。”
“你们究竟在干什么?”
“你去越州了?”
“你不要糊涂了,司马协只是在利用你!”
“裴峋死了,你考不考虑改嫁?”
“章恪!”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一股莫名的沉默在昏暗的房间里蔓延,阿琢皱着眉头看着他,满脸都是愤怒。
章恪抿了抿嘴唇:“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人……”
阿琢有点气结:“司马协勾结晋王,谋反不成,已经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
“我知道。”
章恪轻笑了两声,声音凉薄中带着丝丝寒意,“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怎样的下场。成王败寇,只有胜利者才能书写历史。距谏者塞,专己者孤,我也知道司马协最终一定会败。但是我没有选择,我还有三万人在彬州,他们信任我,以身家性命相托,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他看向阿琢,用极其平淡的声音道:“我得把他们活着带出彬州。”
阿琢抬眸,两个人的视线撞在一起,她仿佛看到他眼中似乎有一片深渊,那重重的责任和累累人命,已经压得他深深浸没在冰冷的寒冬里。
她咽了下口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此时的她什么劝解的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深深叹了口气。
“那你们是怎么出建安的?又为什么来到云州?”
章恪看着阿琢,沉默不语。
“不能说吗?”
阿琢也有点执拗地脾气,“你不说,我也不走,反正向晓也在这,你把我们俩关一起吧,好歹还能做个伴。”
章恪无奈地叹了口气,软下姿态给她倒了杯水:“这个告诉你也没什么……”
原来那一夜,在久安坊,章恪正准备孤身离开,裴峋拦住了他:“全军覆没倒也不至于,能有200残部破城逃回去才更像些。”
他顿时便明白了裴峋的用意,这200余人的残部逃回彬州,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至于剩下的800人,裴峋道:“既然你能相信我,那不如就信得更彻底一些,请侯爷带着这800人在云州安顿几日,到时候会派上大用场。”
“云州?”
阿琢喃喃自语道,“云州这里会有什么大用场呢?……啊!”
她突然叫了一声,“难道是武卫营?”
阿琢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武卫营戍卫东都垣城,距离此地只有十几里地,和守备营一东一西拱卫建安,因此兵力比守备营更多些。
河间军攻城的那个夜晚,武卫营有2000人的兵士提前抵达建安东城门外,虽然最终没有异动,第二天又返回了垣城,但是很难说它不是在观望战况,伺机而动。
这样一想,更觉得那个夜晚的建安危机四伏,被强攻的西门、有内奸的北门、被暗戳戳观察的东门……
阿琢有点后怕,随即又想到:“可是裴峋已经……”
死了……
章恪看着她瞬间暗沉下来的神情,目光也跟着暗淡,这个时候说不羡慕裴峋那就太违心了,你都死了,怎么还能让人对你念念不忘呢?
阿琢又想起来脖子上的玉牌,伸手就想要拿下来:“这个玉牌,我看他们身上都纹了这个图案,不知道它竟然这么重要,还是还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