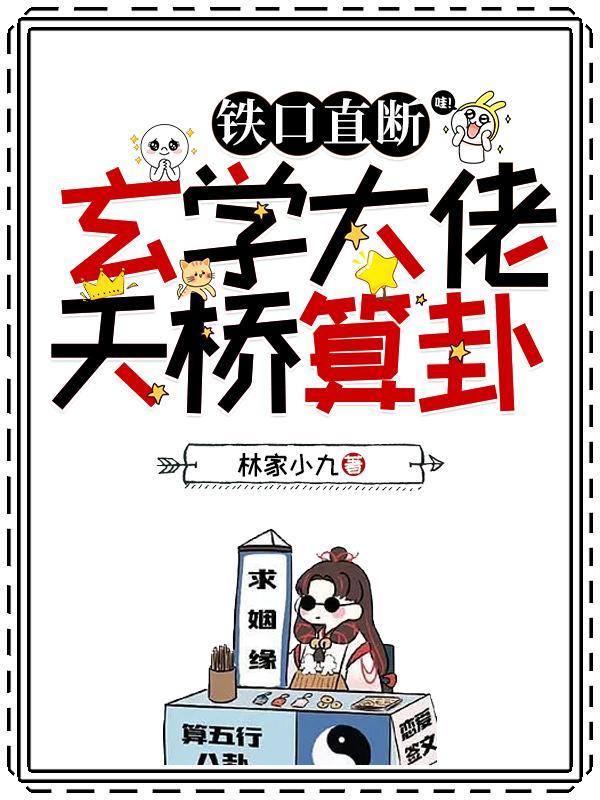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穿越射雕英雄传成为郭靖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融融,使不得的,我……”
欧阳克伸手去握黎融的手,又想将那瓷匙从她手里取过来。那模样十分可爱,黎融仔细去看,觉着他耳尖仿佛也红了,便不禁咯咯笑道:“你怎么这么害羞啊?这原无妨的,你胸前有伤,自己来吃势必是不便的,我喂你几次又有何不可了?”
“我……不惯……”
他脸上又显出了那有些无奈又有着讨好意味的笑。那苍白的脸上突兀的红,落在她眼里,越感到那强者小小的腼腆是如何的可爱。把他看成是一只小猫,曾经在小区里抚摸过的白色的小流浪猫,那白绒绒的毛和依赖着的磨蹭,还有片刻感到了那从不曾感受的温柔之后突如其来别扭着离去的尾巴。黎融歪着脑袋看他,快乐的笑道:“哎呀,过后更有的你不惯呢。如今你就先将就一下罢了。”
这话说得甜腻腻的,加之她那笑吟吟的神色,叫她整个人仿佛都化成了一块饴糖。欧阳克突然想要抱抱她,那细细的,却不容忽视的冲动让他暂且忘掉了那别扭和羞赧,怔怔的看着她,无意识地张开嘴,含住汤匙,粥融化在口中,有香甜的味道,那温热的,香甜的,像面前的女孩子一样的……
多奇怪,多奇怪,这心里所思所想当真可以影响身体上的感受么?欧阳克脑海中胡乱思量着,想到曾经似乎听过一些医者所说的这样的论调,但彼时他是不置可否的,如今仿佛正像是要他认同这论调一样,他素来是个相信自己的人,便让他自己亲自感受这力量。方才的反胃和疲惫都似乎一扫而空了,或许那些不适还在,只是被这爱驱逐到了某个连自己也难以感受得到的角落呢?欧阳克笑了,爱是会改变一个人的,无论是身心,突然开始有些理解自己的母亲。
脑海里浮现出“幸甚至哉”
一类的话,突然感到自己是这世上的幸运者。曾经的三十余年,这是与欧阳克绝缘的想法,同样,此刻的他突然对一切都有所改观,从前对于男女痴爱的一类故事他是最不屑的,但如今却不同了。情愿在这柔软的温情之中粉身碎骨,死亡在这爱面前成了可以被蔑视的存在,理解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理解了苏武和其妻子,理解了“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理解了“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
。
理解了从前无法接受的一切,那兴奋感是混杂着欣慰的,仿佛是小孩子解开了一道思虑良久的数学题目,带着雀跃和欢欣。
他去握黎融的手,这咀嚼的空档,倏然涌出了泪水。黎融被惊着了,放下手中的汤匙,急着问他怎么了,是不是哪儿疼哪儿不舒服,他只是在这模糊的泪意之中抬头,绽开一个彻底而灿烂的笑容。“融融,我很欢喜,”
他颤声说,“原来,我这一生,还是这样的幸运,原来,这世上,当真有这好的情谊……”
就像在冰天雪地之中赤身行走的人,脸庞被霜风刮出血痕,怀中尽是冰雪,倏然来到一间暖暖烧着炭火的小屋,也会有生理性的反应一样。但这时,安然处于这温暖之中的人,再从这屋中的窗子去望外头飘摇的雪时,或许还有恐惧,但也已经可以心存希望地活着了。
“融融,使不得的,我……”
欧阳克伸手去握黎融的手,又想将那瓷匙从她手里取过来。那模样十分可爱,黎融仔细去看,觉着他耳尖仿佛也红了,便不禁咯咯笑道:“你怎么这么害羞啊?这原无妨的,你胸前有伤,自己来吃势必是不便的,我喂你几次又有何不可了?”
“我……不惯……”
他脸上又显出了那有些无奈又有着讨好意味的笑。那苍白的脸上突兀的红,落在她眼里,越感到那强者小小的腼腆是如何的可爱。把他看成是一只小猫,曾经在小区里抚摸过的白色的小流浪猫,那白绒绒的毛和依赖着的磨蹭,还有片刻感到了那从不曾感受的温柔之后突如其来别扭着离去的尾巴。黎融歪着脑袋看他,快乐的笑道:“哎呀,过后更有的你不惯呢。如今你就先将就一下罢了。”
这话说得甜腻腻的,加之她那笑吟吟的神色,叫她整个人仿佛都化成了一块饴糖。欧阳克突然想要抱抱她,那细细的,却不容忽视的冲动让他暂且忘掉了那别扭和羞赧,怔怔的看着她,无意识地张开嘴,含住汤匙,粥融化在口中,有香甜的味道,那温热的,香甜的,像面前的女孩子一样的……
多奇怪,多奇怪,这心里所思所想当真可以影响身体上的感受么?欧阳克脑海中胡乱思量着,想到曾经似乎听过一些医者所说的这样的论调,但彼时他是不置可否的,如今仿佛正像是要他认同这论调一样,他素来是个相信自己的人,便让他自己亲自感受这力量。方才的反胃和疲惫都似乎一扫而空了,或许那些不适还在,只是被这爱驱逐到了某个连自己也难以感受得到的角落呢?欧阳克笑了,爱是会改变一个人的,无论是身心,突然开始有些理解自己的母亲。
脑海里浮现出“幸甚至哉”
一类的话,突然感到自己是这世上的幸运者。曾经的三十余年,这是与欧阳克绝缘的想法,同样,此刻的他突然对一切都有所改观,从前对于男女痴爱的一类故事他是最不屑的,但如今却不同了。情愿在这柔软的温情之中粉身碎骨,死亡在这爱面前成了可以被蔑视的存在,理解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理解了苏武和其妻子,理解了“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理解了“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
。
理解了从前无法接受的一切,那兴奋感是混杂着欣慰的,仿佛是小孩子解开了一道思虑良久的数学题目,带着雀跃和欢欣。
他去握黎融的手,这咀嚼的空档,倏然涌出了泪水。黎融被惊着了,放下手中的汤匙,急着问他怎么了,是不是哪儿疼哪儿不舒服,他只是在这模糊的泪意之中抬头,绽开一个彻底而灿烂的笑容。“融融,我很欢喜,”
他颤声说,“原来,我这一生,还是这样的幸运,原来,这世上,当真有这好的情谊……”
就像在冰天雪地之中赤身行走的人,脸庞被霜风刮出血痕,怀中尽是冰雪,倏然来到一间暖暖烧着炭火的小屋,也会有生理性的反应一样。但这时,安然处于这温暖之中的人,再从这屋中的窗子去望外头飘摇的雪时,或许还有恐惧,但也已经可以心存希望地活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