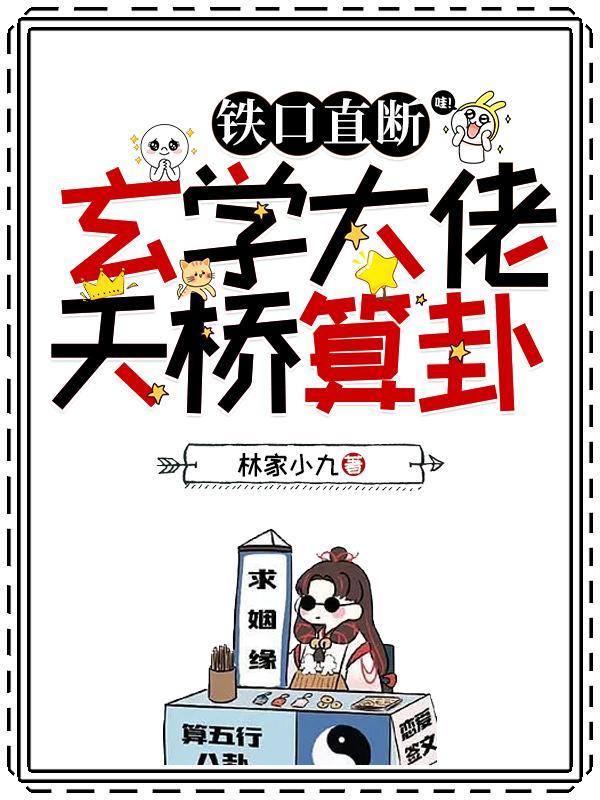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又俗又酸 作者不辞殷 > 第45章(第1页)
第45章(第1页)
喻枞拼了命地压着哭腔,在一条替他而死的生命面前,他要剥夺自己软弱的资格,“你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每天晚上都能梦到那场火,你打电话的时候我醒了,我听到了。”
“宋屹川以为你真把我当回事,所以他杀不了你就来要我的命,而我阴差阳错地逃了,付出的代价只是断了手,可我欠的这条命和那些人身上一辈子都好不了的烧伤,我拿什么去还给人家?啊?我拿什么还啊!!”
喻枞脱力地跪倒在地,拳头一下一下砸在地面上,滚烫的眼泪掉下来,溅碎成细小的水花,孤零零散在那么一小块的地板上,任谁轻轻松松地抹一下,就再也没了痕迹。
他们这些普通人的泪水和性命是一样的脆弱,但凡被所谓人上人的仇怨稍稍牵扯一点,能留个粉身碎骨都是好运了。
“我被你彻头彻尾骗了一场,竟然还能保下一条命来,也真是顶天的幸运。”
喻枞轻声喃喃着,“我本来不是没发现的,我早该意识到,你拙劣的谎话漏洞百出,甚至不屑于编个像样的理由。”
那个仓惶得知了真相的夜晚,他用一个草率的耳光结束了自己生命中最难堪最羞耻的时刻。拼尽最后一丝求生的力气捡起自己的尊严,密不透风地裹住遍体鳞伤的身躯,把本该好好上药的创口熬成了腐烂的毒疮。
现在他终于熬不下去了,就如同冷硬到极致却失了韧性的坚冰,在内心深处的地火孤绝地爆发的这一刻,无法挽回地破碎了。
“我早该意识到的……可我把你看得太重要,比我赖以为生的思考能力更重要,你撒一句轻飘飘的谎,我就不管不顾地相信你了。”
“我以为你会一直傻下去,所以我从来没图过你任何回报,我以为这样就算做足了心理准备,可我没想到你还是回报我了,回报我数不尽的谎言和利用,你把我当保姆,当存钱罐,当充气娃娃,然后还要我当泄愤的靶子。”
“差一点,我断的就不是手而是脖子。”
他好不容易捡回来的一条命,差点又葬送在他曾以为是恩人的宋十川手里。
对喻枞而言,他最恨的哪只是宋十川,他平等地憎恨着过去那个头脑简单的,在爱这个字眼的掩护下放纵愚昧的自己。
“你恨不得把我榨干了,把我的尸体也熬出油来给你的公司增添光彩吧?”
喻枞痛哭到眼泪变冷而双颊发烫,在濒临极限的情绪拉扯中,太阳穴不堪重负地呻吟着,刺得他头痛欲裂。
宋十川终于开口了:“是我的错,我疏忽了。我会找人去处理赔偿的事,该给你的我也没忘,我说过会赔你一套更大的房子,他们该得多少也会得多少。”
喻枞像是听到了另一个世界传来的笑话,他慢慢抬起头,一张布满泪痕的脸对上了另一张没留下半点情绪痕迹的脸。
“房子?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只想要那些东西吗?那套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需要用钱了,让我卖掉,没问题,我不在乎。”
喻枞想站起来,但失败了,他僵硬的膝盖上又传来了幻觉的灼烧感,这幻觉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他已经难以分辨它的来源——是前世的那场火,是今生的爆炸,还是宋十川造下的孽缘?
“可是你打翻我给你做的饭是为什么,你一次次装疯卖傻,弄得我浑身是伤又是为什么?是考验我吗?看我对你是不是真心实意不离不弃吗?”
“宋十川,”
喻枞发誓这是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念出这个名字,“你、算、什、么、东、西、啊?
宋十川看着他弯曲的脊背,看着他凌乱的头发下露出一双黑得不见底的眼眸,这幅被痛苦反复碾过的狼狈姿态,像游魂一样飘到了他铜墙铁壁的心防前。
那是他亲手制造的痛苦,而他却茫然地旁观着,理所当然地拒绝去与那只游魂交流。
可这一次,他如臂使指的回避系统好像失灵了,因为他忽然闻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宋十川最近总觉得喻枞身上多了一股让他觉得非常非常好闻的味道,让他像上瘾了一样痴迷,明明喻枞是个没有信息素的beta,明明他们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洗护产品,可那股味道依然固执地只肯停留在喻枞身上,吝于分给他一丝一毫。
哪怕他拿着喻枞换下来的衣服,那气味也像是遇到天敌一样地逃跑,消散的速度快得令人吃惊。
而现在,宋十川发现那个味道改变了。
它像是掏出了一把纸裁的玩具小刀,扮家家酒似的在他面前挥了两下——
下一瞬间,他用十几年构建的铜墙铁壁就像柳絮那样轻飘飘地散了,他怯懦的堡垒轰然崩塌,他和他亲手制造的游魂之间再也没了距离。
他赤身裸体再无防备,让那抹游魂钻进了他的心里。
在宋十川的意识回过神来之前,他的心已经无药可救地翻搅起来。
宋十川痛得弯下腰去,他和喻枞的关系从俯视变成了平视。
在他终于找回了正常人的同理心,终于可以触摸到另一个人的情感和温度时,迎接他的,是曾经最爱他的那个人所赠予的最刻骨的恨。
喻枞曾经是全世界最爱宋十川的人,可宋十川知道得太晚了,他的爱早已变成了反复扎透骨头的冰刀,要想拔出他心头的憎恶,宋十川得先捱十几轮扒皮抽筋。
那双无数次注视着宋十川的温和柔软的眼睛,因为憎恨而改变成了陌生的形状,可恨到极致时,那双眼睛竟又重新变得熟悉了。
不是像喻枞,而是像宋十川自己——像那个被仇恨扭断了所有温情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