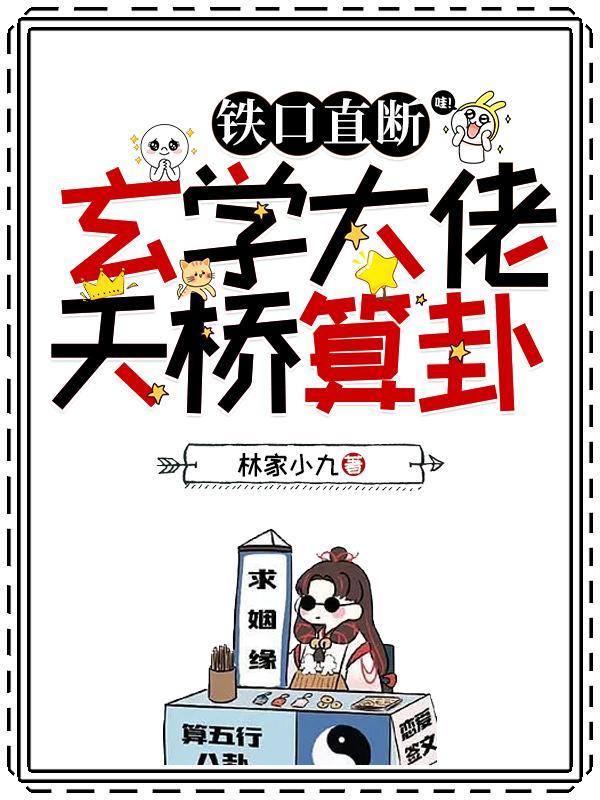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将令行 醉酒风化 > 第56章(第1页)
第56章(第1页)
他把杯子推给黄莲拙,眉眼弯弯,却让人骤升寒意,好一张笑面虎。
不是个好打发的上司,黄莲拙心里揣摩着他的用意。
胡主簿低埋着头,看了黄县丞一眼,赖着脸皮一直没敢吭声。
黄润拙知道他是个软骨头的,当下心里也是一个火起,没好口气说:“今年天灾,种地收成都不好,哪里又敢催紧了那些刁民,万一弄不好一个揭竿反了,属下我担待不起那个罪过。”
说罢,他喝了口酒。沈遇问:“好喝吗?”
黄莲拙不解他话外之音,下意识点了点头说好喝。
“律法有规,衙门内不得设酒。”
沈遇心平气和地提醒,“杖二十。”
黄莲拙吞也不是吐也不是,猪肝脸色。
沈遇却又友声道:“喝吧,算我请的,谁定的这破规矩,大冬天还不让人喝口暖和的了。”
他脸上带着淡淡的戏谑。
胡主簿为着这一出心里绷着的弦也松了些下来,觉得他是个好脾气。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沈遇将酒竹提放下,“我们这些个当官的,就是夹在中间的行策,执行、下令、调渡、缓和,是操劳为难了些,可手上的府印也是实打实的捏着,本县目前也没看出二位有还自由身的想法。”
他依然很好口吻地说:“大今律法,二月查税,不符制者罢官贬谪,乃至抄没家财入库。本县一穷二白,不想我到时拉你们出去一同顶罪的话,就快去做事吧。”
算是恩威并施了,用词也并不让人难堪,黄莲拙顿时哑口无言。
他同姓胡的对视一眼,都在彼此眼里看到了忌惮。
简单又是几句嘱咐,沈知县总算是放了人。
屋外,又是漫天飞雪,同黄莲拙一齐出门的胡主簿回首望了眼中堂,叹了句话说:“后生可畏,我看这沈老爷是个厉害的,你我日后恐怕是有得劳碌奔波了。”
黄拙莲:“哼,看个茶都要行贿的人,我看他方才就不是个做事的态度,分明是变着法地向我们讨孝敬呢。”
“县丞此话当真?”
胡主簿锤着肩膀,捋了把胡子叹气,“若他真是个使钱就好相与的,我还真松了口气,就怕他像王知县那样,心有余力不足,事没办成人也昏沉,上下搅合得一片浑,把巡抚衙门里头的大老爷们得罪了个遍,搞得每次省里来人都不给我们好脸色瞧。”
“且拭目以待吧。”
黄莲拙拂袖出了去。
然后便再没见着黄县丞和胡主簿两人了。已近晌午,沈遇抽空歇息,便收了茶具,去茶房自己洗着,听到门房外传来嘈杂的议论声。
“那边仗打得好凶,据说站城门口都能闻到血腥味呢。”
“是真的。”
有个人说得煞有其事,“吓人得很,我二姑家里那个,昨天晚上三更回来了,右腿都被元人砍了一只,战场上装死才捡回一条命的。还是我二姑使了好些银子给他那伍头,那边才肯消籍放人,划了名字让上头以为他战死了,要不然缺了条腿还得继续上阵打。”
“啧啧,还好我早地进了衙门,不然到时候募兵也有我的份。”
“我也是,家里就我一根独苗,我要是没了,我爹娘还不得哭死。”
“据说关林那边更惨,萧家铁骑去救落雁山,十二个烟台上根本没有巡逻,那简直无异于是将西脉拱手相让,我还听说萧老侯爷受了埋伏身受重伤呢。”
“我嘞个娘啊,自己的家门都不守,李家双侯在干什么啊?咱们大今不会要亡了吧。”
“但是裴老带的沙骑营打得好,已经快把敌人给逼出大今国土了。没瞧见么,头上一撮红毛的驿丞天天跑,传上去的都是战讯捷报呢。”
“我表哥在军里,中午给家里来了信,据说今晨就是好一场血战。元军那边把大炮拉出来了,狮子岭都快被轰平了烧得那叫一个火海茫茫,正当元人以为势在必得之际,谁知道裴四少爷率兵突然从地下冒出来,杀得他们措手不及,在场之人无不说那简直是生死一线,天兵下凡,是武神附体裴四少爷救他们来了。”
“光是想想都觉得心潮澎湃啊。”
“威风,虽然我不敢上,但是我是真觉得威风。”
沈遇听之,淡淡一笑,狮子岭下有空穴来水,心道他定是借助了地势,发现了下边的地道或者可容纳兵卒的地方,什么天兵下凡,武神附体,只是裴四占据先机捞了个大便宜而已。
洗罢,他出了茶房,吓了几位差役一跳,都纷纷与他微笑问好,目送着这位一言不合就拉出大今律法恐吓的沈老爷走掉。
不过他看似仿佛心情很好。
衙门没有伙食,兰许也当兵去了,屋里没人给沈遇送饭,于是孤单的沈大人,只好拎起退不回去的菜篮子,热了锅水吃了五个烫鸡蛋下肚,竟生生地撑到了晚上还没饿。
沈遇看完卷宗,天色已经渐晚,他正剪了一截烛芯,却见今早那替他跑腿的差役,擦了擦汗神色慌张喘着粗气奔赶而来。
“沈老爷!”
那差役一个不留神被门槛绊到,“出事了!出事了!玄公门那边闹民变了!好几个汉子都跟衙门里的官差打起来了!”
莫非是为着收税的事?沈遇即刻起身,拿了案桌上的官印走。
玄公门,是门又不是门,准确的说是块残破的石柱,据说乃是数年前一名清官所修筑,因其清正廉明的品格和威望故而得名。离沈遇租的住处很近,他很快便寻到了。
远远看去,人头攒动,围成一团,火光点点,四下局面凌乱嘈杂。
乱局为首之人是个粗犷的汉子,操着一把砍刀,架在个官差的脖子上,正是汗流浃背的县丞黄润莲,汉子一面胁迫官吏、一面吆喝民众道:“借玄公英名在此!我周大勇今天就要问问各位官爷!自大今开国三代以来,朝廷征税一直是年计二两银子,二两银子,对官爷们可能算不得什么,可咱老百姓的家里省吃简用,二两银子抵得上咱一个月的开销有余!犹想玄公当年在时,也不是没遭天灾农难,可他哪怕自己咽烂菜也决不取百姓一分一毫!怎么如今,朝廷富足,官爷们竟还将税生生地追加到了五两银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