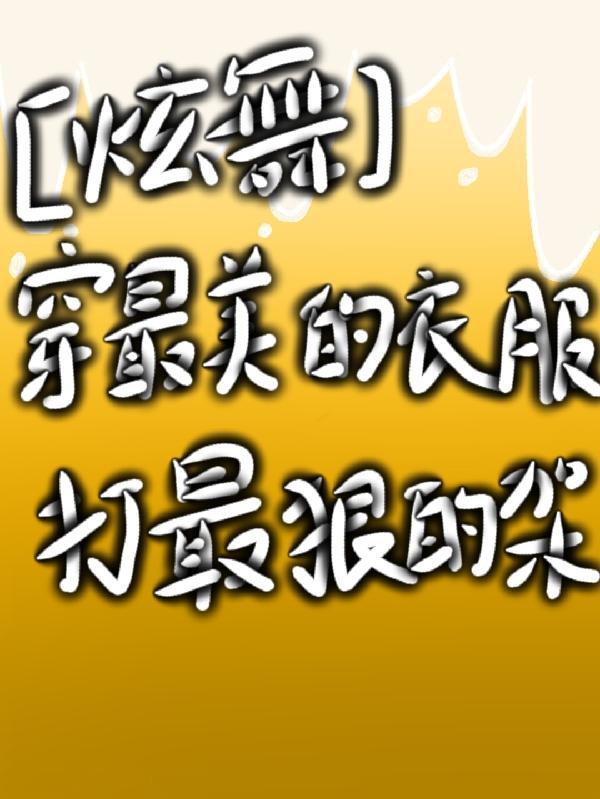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将令行免费阅读 > 第21章(第1页)
第21章(第1页)
锦衣卫见之握刀不动。
阁老拂袖,露出轻松的笑意起来:“你小子好自为之吧。”
几位肱骨悄然离去,沈遇看着他们的背影默不作声。
裴家姑娘们可算想起来,去找夏老拿书去了,院里只余下裴渡和他。敏锐的裴四哥察觉到他脸色不对,指背碰了碰他的额头问:“你吓着了,脸怎么这么白?”
“有事说事。”
沈遇拨开他的手,古怪地瞪了他一眼。
裴渡敛了笑,略有正色问道:“见着海阁老,怎么是这个反应?锦衣卫不像是要你小命的态度。”
“我怎么知道?”
沈遇搪塞。裴渡抚着下巴,揣摩着没说话,二人陷入沉默。沈遇又出声打破沉寂:“萧家那边,燕淮的粮也吃紧么?”
“可问对人了。”
裴渡唇角一勾,像是显摆自己的学知,“燕淮的粮啊,就没有一天不吃紧的。”
“平云野除了草,什么都活不了,八千沙兵吃的都是燕淮借的粮,我们这些个咽残羹食烂菜替朝廷卖命,上头发下来的军饷却连点荤腥都见不着。落雁山为什么被烧?海阁老笑得好,我也觉得烧得好!禾东总督贪多了,不赈灾是拿不出粮来,又怕朝廷下来问罪,自己反而先把自己给吓死了。襄水灌溉泽南禾东,他们就是一体的,王大壮是个勇士,是替禾东禾泽南的百姓讨公道!谁不知道驻关李家是皇家亲眷,不管是去借也好抢也罢,敢动他们就是打圣上的脸,事情不大,才就怪了。”
裴渡呵了两声,摩着拇指上的韘,带着他的狠辣又莫名的笑。
他手上的韘是来自落雁山的青木,质地坚硬,色泽亮丽。据说驻关李家和沙骑裴家不和,便是因为这座入今之要塞。
庸都背后的命脉落雁山,乃是当之无愧的大今命脉。不仅是灌溉禾东泽南的襄水源泉,更是上御西壤赤部下接陇西高原的天然城墙。当初成乾先帝登基之后恐外戚生变,倚信本家,将此等关口重地交给了年轻的李家双将,反而冷落了立下赫赫战功的两位老将军,将裴萧两家驱至了贫苦的云庭和燕淮守关林御外邦。
沈遇斜着眼睛看他,心里思量着什么,好半天吐出一句话:“受教了。”
而后裴四哥又恢复了他的轻浮嚣小模样:“关心燕淮做什么?我裴家待你不好,沈哥儿又打算去萧家当伴读了?”
沈遇没说话。裴三姑娘抱着几问他:“沈哥儿,夏先生问你这琴要不要?”
裴五姑娘提着裙子下来,眨巴着双明亮诚挚的眼睛说:“听夏先生说你也会弹,你倾囊教教我可好?”
夏康倚在门边,对沈遇点了点头,青袍双袖迎风自舞飘动。
“一曲《雁孤行》,算是替你日后送了行。”
他提高了音量,抱着琴下了来递给沈遇道:“要收好,这是先帝爷赏我的,选自陇西上的守心木,音色纯质透亮,可谓是万金难求。”
沈遇郑重接过,听出了他言外之意:“那便谢过夏先生了,学生一定不负所托。”
他一行拜别夏康。两姑娘上了马车,落在最后的沈遇抱着琴若有所思,沉吟道:“夏老表字开疆,为先帝爷出谋划策,位列宰辅封疆入阁,也真是题了个好兆头。”
“沈宴清又何必妄自菲薄?”
裴渡半个身子露出,撩开帘子像是请他同座。
沈遇佝身上去,谁料裴渡只是接了他手里的琴,而后又露出个没心没肺的笑来:“这琴就占了好大的地儿,又只好劳烦沈哥儿屈尊外头了。”
雁孤行
马车平缓地行驶着。沈遇昏昏欲睡,突然听到了骏马快蹄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不多时,裴铭和郑芳绪一身风尘地追了上来,他发现二位长辈的脸色都不大好看。
隔帘被撩开了,传出姑娘们热切的嗓音:“爹。娘。”
“大夫人。”
二人才从平城巡抚衙门回来,见着小辈们便正好同路回家去。沈遇听见了裴铭带着怒气的嗓音,道:“何必昌个废物草包,他就是怕得罪那黄崇禧那太监,实在不成我们带人闯储司抢粮去!都入冬了即便钱拨下来也晚了,燕淮的粮也早在秋分后就卖完了,再这么拖下去沙兵们明天连稀饭都喝不上了!”
“将军,办法得慢慢想,越到这种时候越不能急。”
郑芳绪说。
裴渡问道:“爹,大夫人,云庭的局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么?”
裴铭对儿子都不掩心中烦躁:“云庭知县都挑撂子不干了,空着个位置朝廷也迟迟不派人下来,你说呢?”
还未上任的沈知县指尖一动,摩挲着袖子里的官牒没有言语。
云庭处在平云野腹中,遍地荒草石沙,根本种不了地,连常驻的百姓都很少。唯有沙兵,和要练军的裴家为恪尽职守不得已住在这穷乡辟岭。
燕淮在关林附近,好歹有草有水有田地。
“燕淮的粮呢?我们不是还买了地吗?实在不行还有萧家接济呢。”
裴亭竹问,也说出了沈遇心中的疑问。
“不行!别打萧家的主意!”
裴铭义正言辞,“燕淮今年收成不好,我们买的屯地也就够吃三个月,那也都是托了萧家人情才划给我们的!今年谁都不好过,他们都苦到去刨关林了,我们做兄弟的不能再不厚道!”
郑芳绪的嗓音显得苍凉:“将军,哪里够三个月,则怀不是才写了信,分明只够一个月了啊。”
“缺粮就罢了,都落雪入冬了,军用冬衣也要给官兵们添置,朝廷的人难道就不管我们死活吗?”
裴嫣然带着悲悯和失望。
裴亭竹恨声显得暴戾:“我们在前面卖命,那些个狗官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