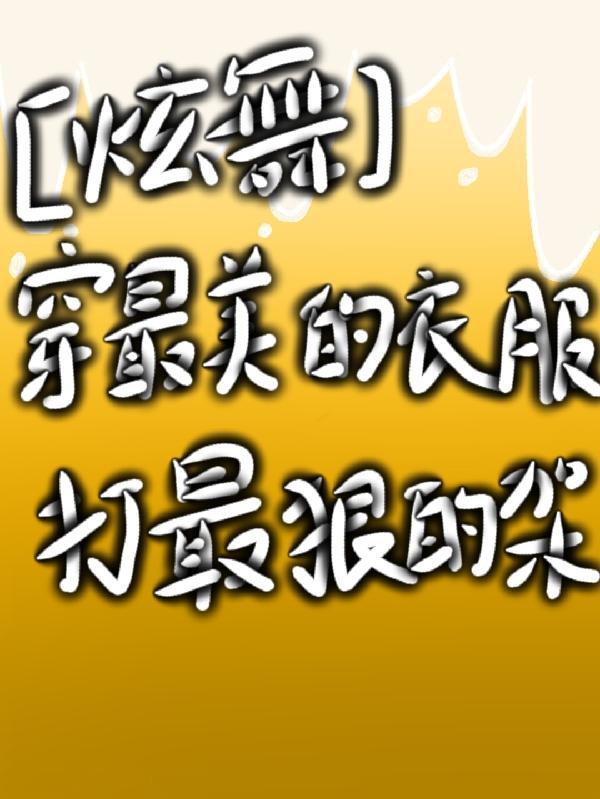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鉴定所鉴定严重错误 > 第83章(第1页)
第83章(第1页)
但还是将爱徒吓的双腿一软,差点又泪如雨下,如果不是蒋幼柏哭声太大的话……
“老祝她真的好惨吶。”
刘清山默默瞥她一眼,眼中流露出一丝同情。她迅速收拾好药箱,准备离开。但凤思霜却拦住了她的去路。
“住所已为神医安置妥善,”
凤思霜凤眸盈出淡淡水光,声音带着一丝无力:“还是要劳烦神医想想办法。”
刘清山的脸颊微微抽动,幸好他年事已高,皮肤松弛,不易被人察觉他的情绪波动。
彼时的祝佩玉正咬着笔杆子凝神看着京城的地图,书中只说凤思楠的根据地在城外的一处偏僻地,但这范围大了去了。
大皇女三个月的禁足马上临近尾声,她要抓紧把这地儿翻出来,让老大去举报她。
搞不好,一直斗的乌眼青一样的老大老五,能够统一战线一致对外。
凤思楠不是最喜欢坐山观虎斗吗?倘若有一日她置身于角逐场内被双虎斗,看她还笑不笑的出来!
祝佩玉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正美滋滋的幻想那场景时,房门‘嚯——’的一下开了。
祝佩玉条件反射地跌躺在藤椅上,手肘不经意磕到了扶手,疼的她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只能呲牙抚着胸口,咳嗽得气若游丝:“也不知我这是怎么了,才站了一小会儿就感觉全身无力。咳咳咳……”
搁在平常,温心早就小跑过来扶她起身嘘寒问暖了。可祝佩玉咳了好久,来人都没有理会。她的心头一跳,一种被忽视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她狐疑地歪过脸,意外对上了刘清山森冷摄人的脸。
祝佩玉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她嘿嘿一笑,试图缓解紧张的气氛:“您老什么时候来的?”
说着,她一骨碌爬起,为她搬了一把椅子。
刘清山冷哼一声,取出药箱里的银针包展开:“老身瞧你这病也是辛苦,不妨给你来几针,早日解脱了吧。”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断,让祝佩玉感到一阵寒意。
祝佩玉原以为她是开玩笑的,没想到她真的捏着一根超粗的针头,作势就要往祝佩玉的身上戳。祝佩玉看着她手里的针,惊恐地连连退后:“刘、刘……刘神医,您莫冲动。”
刘清山继续逼近,直至将她逼近墙角:“针是粗了点,但你已病入膏肓了,针粗见效方快。”
她的声音冰冷,没有任何情感波动,仿佛在处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说罢,对着她狠狠一扎。
撕心裂肺的哀嚎声响彻整个后院,午睡的鸟儿惊恐展翅,不多时,只剩下一根羽毛缓缓落在庭院的石子路上。
房门吱——的一声开了,看着迎面而来的三张脸,刘清山淡定地拢了拢衣袖:“老身也是第一次行此针法,没想到起效甚快,祝吏书已经好多了。”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满意的微笑,仿佛对自己的手法颇为自豪。
三人登时眼睛一亮,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温心喜极而泣:“多谢师父。”
蒋幼柏握拳一碰,脸上洋溢着敬佩之情:“果然是神医,一出手方见真章!”
凤思霜正色点头,追问:“如此?祝吏书有痊愈希望了?”
“嗯,就是此针法太过刚烈,且行针时一次比一次痛苦。”
刘清山缓缓回头瞥了眼惊魂未定的祝佩玉:“还是要看祝吏书的身体能不能抗的住啊。”
祝佩玉:“……”
温心摸去了眼角的泪痕:“有徒儿陪着她,她定能战胜病痛。”
蒋幼柏脸上带着乐观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祝佩玉康复的那一天:“不过是扎扎针而已,我相信老祝一定能挺过去!”
凤思霜探头进去,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祝吏书,本王命你坚强一点,否则本王就砍了你的脑袋。”
祝佩玉欲哭无泪、瑟瑟发抖:已老实,求放过。
祝佩玉压根没病,她两个多月前突然端着碗汤寻到了刘清山那,询问那汤是否有问题。
汤没问题,只是那汤中的枸杞加入了碎肝砂。此毒一旦体内毒素积累,肝脏的解毒功能就会下降,造成血管脆弱,引发流鼻血等症状。
只是并无凶猛,中毒者不会很快毙命,甚至前期很难让人察觉到什么异样。
所以刘清山教了她一招,在她需要流鼻血时,吃上她调配的药丸并扎自己一针,便能流鼻血不止。
她面色发白,纯纯是血放的多了;至于咳嗽手抽筋,刘清山以为她就是欠揍了。
她的济世堂还有大把的患者,哪有功夫陪祝佩玉胡闹,收拾了她一番后,忙不迭的离开了安北王府。
只是马车刚入闹市,就被迎面而来的马车拦住了去路。
看着车厢内的凤思楠,刘清山淡淡道:“礼公主这是何意?”
凤思楠嘴角浮上一层笑意:“想刘姨了,所以想请刘姨过府一叙。”
说的是请,但语气坚决不容有辩,刘清山坐的四平八稳:“老身不甚荣幸,只是济世堂事务繁杂,老身实在抽不开身,望礼公主海涵。”
凤思楠笑意敛起,一脸悲意:“在隐瞒磐宁疫疾一事上,本宫确然有错,刘姨待本宫从来亲切疼爱,如慈母一般。”
她放缓了声气,柔声道:“稚女犯错,您再如何生气,随意责骂便是,因何不能原谅?”
刘清山抬了抬眼皮子,语气中带着一丝讽刺,显然对凤思楠的言辞并不买账:“礼公主折煞老身了,您乃天之骄女,凤女凤孙。老身万万不敢以慈母二字自居,那可是要掉脑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