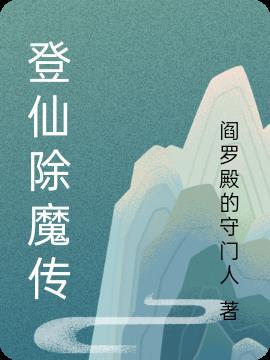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偏航谢凌云戚乔全本免费 > 第58章(第1页)
第58章(第1页)
“别想有的没的。你爸把你扔给我不是让你放弃自己。”
因为看不见的缘故,潘多拉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冷漠无情,“你的手机坏瞭,我帮你把资料拷贝到新手机。有什麽想要联系的人?”
药效和失明可能性带来的双重副作用是她变得格外暴躁。但她不会跳脚,也不会胡乱指著空气破口大骂,而是整日一言不发地躺在病床上,就好像她不是瞎瞭,而是哑巴和聋瞭。
潘多拉无奈提高音量:“没死就应一声。你应该有想要联系的人?”
鬱理转过脸。蒙著双眼的白色纱佈已经摘下,她戴著硕大护目镜,皮肤和嘴唇一样苍白。
她不答反问:“消息捂住瞭没?”
潘多拉表情複杂。她们出事地点很不妙,位于市中心,消息尽力捂瞭,但时间差的关系,仍是流传不少现场照片。
所有发佈在网络上的照片,潘多拉一一核验,确定没有一张照片露出鬱理和joey的脸。
但媒体就像嗅到血迹的苍蝇闻风而动,迅速关联前后始末,再通过大秀当天流露的照片,隻花瞭三小时精准定位伤者。但最有影响力的报道没出,潘多拉砸钱堵上他们的嘴。
鬱理不想再听和事故有关的任何词语,她怀疑自己有点ptsd。
她不知道自己住院瞭多久,时间变得没有意义。她现在的眼睛不能感光,别想碰手机,潘多拉把所有电子设备收走。
好消息是joey情况终于好转,她勇敢地活下来瞭。
鬱理终于松瞭一口气。一月气温很低,但她连感知寒冷的能力也失去。
她捂住自己心口,一点一点,在看不见的夕阳馀烬中,缓慢沉重地躬下身。
不能掉眼泪。鬱理反複警告自己,如果还想保住眼睛,绝对,绝对,不能掉眼泪。
“到底有没有?”
她感觉床侧塌陷,潘多拉坐下来,似乎想揽一下她的肩,但不知为何,动作生生止住。
许久,久到潘多拉开始不耐烦,终于听见她气若游丝的声音。
“没有。”
旧噩梦
鬱理向来不喜欢阅读任何卖弄苦难的书籍,管他是莎士比亚还是契科夫。
她出生在一个享有名誉和财富的傢族,五岁收到的生日礼物是傢族信托和一座位于海德堡的黄玫瑰庄园。
德意志民族的刻板严谨深入骨血,但,过犹不及,schwarz傢族出瞭一个叛逆昭彰的疯子。
她的人生是一场公开上演的大型行为艺术。她为自己选定伴侣,怀孕,生育,然后把女儿视为创造的艺术品。
那个拥有如土地厚重的棕发小女孩儿,如此天真,如此单纯,如此美丽。
alessia把她关在特意为她量身定制的精美玻璃水箱,搁上漂亮干净的鹅卵石,还有几尾惊慌失措的红色金鱼。
然后,打开水闸。
小姑娘茫然失措地站著,水箱不大,隻能容纳她转身,却无法令她逃跑。
她又开始求饶。
樱粉棕的眼眸蓄出眼泪,顺著眼尾淌到粉白两颊,紧接著被alessia突然加大的水流冲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