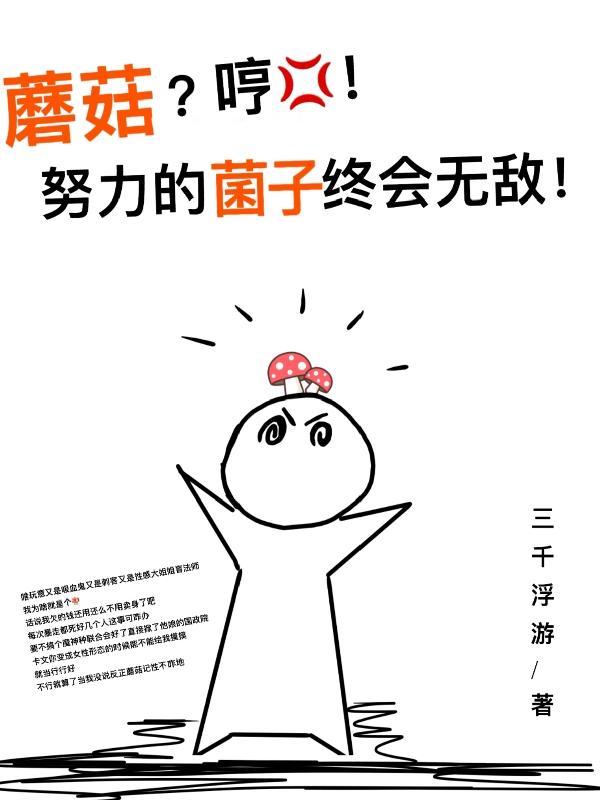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同桌别走 > 第30章(第2页)
第30章(第2页)
“没有为什么。”
迟绛闷哼了一声,挪着椅子往左边坐了坐:“到十句了。”
讲话额度在大清早就浪费完,闻笙却不以为意。以她对迟绛的了解,撑不过一节课她就会主动开口。
然而,一节课过去了,一个上午也过去了,迟绛却还在执拗地紧抿嘴唇,坚持不肯和闻笙讲话。
闻笙有点慌张,几次想要开口,可两人四目相对的瞬间,她又不知该讲些什么,只好默默将目光移开。
更令闻笙担心的是下午的体育课。
两人一组的仰卧起坐训练,她和迟绛是固定搭子。话不能讲,肢体接触又逃不开,这令她略感无措。
课间打水时,闻笙也有些心不在焉,以至热水灌得太满,烫到虎口处。幸好学校饮水机水温不够高,烫伤处只是有些泛红。
“闻笙,你是不是在和迟绛冷战呀?”
祝羽捷也在旁边接水,“中午吃饭,迟绛几乎一声不吭,我就感觉她状态不对。”
“这样吗?”
闻笙拧紧杯盖,想了想,又摇摇头:“但是并没有冷战,我们平常就不讲话。”
话是这样说,一回到班级,闻笙就走到迟绛桌边,弯曲指关节敲敲桌面:“出来一下。”
她走在前面,迟绛隔着三步远的距离跟在她身后,直走到无人经过的楼梯中层拐角,闻笙才停下来。
“迟绛。”
她看着对方眼睛,轻声开口:“羽捷问我,我们是不是在冷战。”
迟绛紧抿嘴唇,直视闻笙的眼睛,但还是不肯说话。
她承认,自己就是在生气的,但自己想通之前,不想再和闻笙交流更多。
闻笙擅长阅读表情,不费力气看出迟绛额头闪闪发光的「生气」「要哄」几个大字。
但哄人向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闻笙于是轻轻捏住迟绛袖口,小幅度晃了晃,问她:“可不可以告诉我,今天在气什么?”
迟绛却双臂交叉趴在扶梯栏杆上,低头坚持道:“我哪有那么容易生气,我只是在履行十句话的约定。”
“你不肯说,那我就随便猜了。”
闻笙站到她身侧,低声喃喃:“是我性格不好,今早语气太差劲,对不对。”
“只对一点。”
迟绛总算开口,她告诉闻笙:“但我不是和你闹别扭,我只是和自己生气。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是冷冰冰的个性,又总是自作多情,以为我们可以做朋友。”
闻笙听着“朋友”
两个字,感觉奢侈。像身无分文的小孩站在玩具橱窗前,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却不敢奢望占有。
从念书起,她的生活里就只有“竞争”
二字,妈妈也反复与她强调:“少为无用的人和事浪费时间。”
再一想到那些因为妈妈介入无疾而终的友谊,闻笙的呼吸又紧张起来。与人打交道。她总是小心翼翼,不敢给出丝毫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