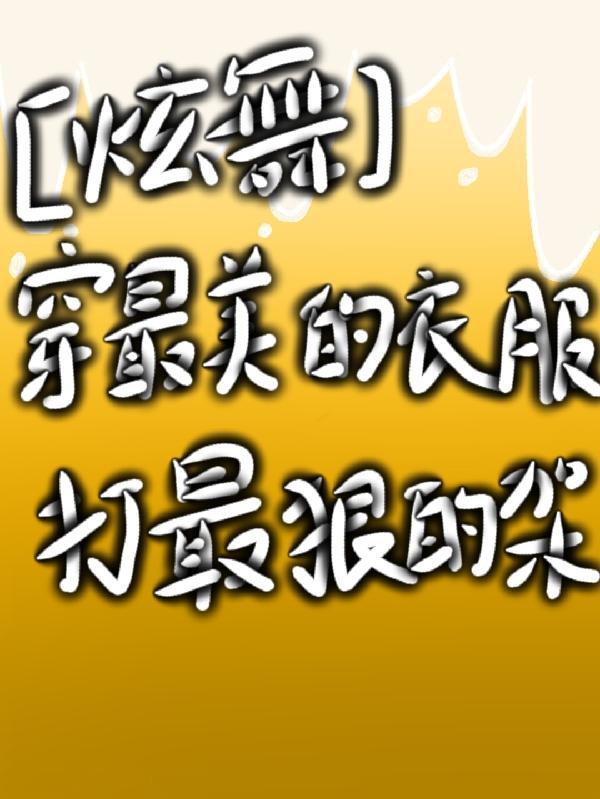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爱谁谁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周通见宋十安败兴而归,问:“夫人如何说?”
宋十安道:“母亲近日身子乏累,头痛不已,想回京了。我没敢在这当口提我和钱浅的事,免得她动怒会加重病情。明日我还是先去见钱浅吧,看她可否愿意与我一同去京都。”
周通担忧地问:“若钱浅姑娘不愿意,公子又当如何?”
宋十安也有些苦恼,“看她是因何不愿去京都。若是不喜京都人际关系复杂,我可以向朝廷申请戍边,带着她和绵绵一同到边关生活。若她不想离开青州……罢了,明日见面再与她商议吧,总能想到办法的。”
钱浅回家后已然累极,躺在床上脑子乱成了一锅粥。
想来不久之后,绵绵继父继母获罪的消息便会传开,即便二人已死、即便绵绵未受牵连,只怕绵绵日后也难以面对人的指摘。将来她不在了,绵绵该怎么办?
胡思乱想着,苏绵绵已做好了简单的晚饭。
二人沉默地吃了饭,苏绵绵见钱浅魂不守舍的,又哭了出来,“姐姐,咱们以后该怎么办……”
钱浅努力稳住破碎不堪的心神,轻声问:“绵绵,你可愿随姐姐离开青州?”
苏绵绵哭着点头,“我愿意!只要能和姐姐在一起,去哪里都好!”
钱浅道:“好,那就去收拾衣裳行囊,咱们明早便走。”
钱浅强撑精神,又去了趟车马行,定了两辆马车。随后去茶馆和书肆,将《修真传奇》的最后两册同时卖了出去。
书肆掌柜问:“江公子快要去参加会试了吧,所以一次性把全本都送了来?那我这次给个好价格,就当提前恭贺江公子高中了!”
钱浅没有否认。
她很需要钱,此刻也顾不得占江远山一点小便宜了,接过沉甸甸的钱袋回了家。
苏绵绵已经按她说的把合身的衣裳都收拾出来了,钱浅挨个儿屋子一样一样看过去,检查需要带走的东西。本以为东西会很多,然而此刻却发现,除了衣裳首饰、乐器和一些书之外,竟也没有多少想要带走的。
收拾的差不多了,苏绵绵累得呼呼睡去。
夜色如墨,不见月晖与晨曦,钱浅坐在院中,忽然泪如雨下。
这几天积压的所有情绪,在这漆黑的夜里,张牙舞爪、肆无忌惮扑来,她分不清是后背疼、胸疼、腹疼,还是心疼,只觉得浑身都痛的要死,疼得她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
无声地哭了一通,她也不知自己坐了多久。
天边的黑色像被稀释了一般,逐渐变蓝、变浅。
钱浅整理好情绪,回屋写下了宅契转让文书,签字按上手印,装入信封中。
车马行的人如约而至,将她们要带走的东西装到马车上,钱浅将家中剩下的米面粮油和蔬菜放到了李婶家门口,留下字条,最后看了一眼宅院,锁门走了。
车夫先赶车去了赵希林家,钱浅将签好字的转让文书连同宅契、钥匙一起,交给了值班的门阍。她不打算再回来,这套宅子便给了赵希林,当做赵希林这次帮忙的报酬好了。
车夫问:“姑娘究竟要去哪?”
钱浅头脑混沌不堪,随便指了个方向,“那个方向,下个城镇。”
车夫想了想,“是去淄州吗?”
钱浅应了一声,“可以。”
马车从西城门驶出青州城,钱浅看着逐渐变小的青州城墙,转过身去,一步一步远离生长之地。
天已渐亮,却灰蒙蒙一片,看不见日头。
一如她此刻的内心,荒芜萧瑟,有种日暮穷途的悲凉。
宋十安早上去看江书韵,江书韵仍然称病,没有见他。
宋十安只得带孙烨出了门,先去找钱浅。
孙烨开心地赶着车,宋十安笑他:“你这么高兴做什么?”
孙烨道:“我当然高兴!钱浅姑娘和绵绵姑娘都是性情好的,每次来我什么事都不用做,还有茶喝、有曲儿听、有果子吃、有话本子看。想一想二位姑娘看到公子康健的模样,得高兴成什么样!”
宋十安脸上扬起一丝笑意。
孙烨又道:“对了,公子还不知两位姑娘的模样呢!这钱浅姑娘啊,五官清丽,皮肤很白,小脸只有巴掌大点儿,身材纤细得很,只有脸上有那么丁点儿肉。绵绵姑娘比钱浅姑娘胖一点儿,小脸肉嘟嘟的,很是粉圆可爱。”
“二位姑娘虽不似京都贵女们那般明艳惹眼,却都是十足的小美人儿呢!”
宋十安嗔他:“用你说?一会我不就见着了?”
二人满心欢喜地来到钱浅家门前,却碰了锁。
宋十安疑惑道:“怎会不在家?难道两日都没能办完绵绵身籍的事?”
他没有太着急,而是立在门口耐心等着。
没过多久,两名衙役突然匆匆赶来,看着落锁的门问:“请问,苏绵绵可是住在这里?”
宋十安神色诧异,连忙问:“是。请问出了何事?”
衙差打量了下他,“你是何人?”
宋十安答:“我是这户人家的家里人,有什么事与我说也是一样的。”
一名衙役道:“今晨有人在白头山的猎户小屋里发现了曾小娥夫妇的尸身,虽然苏绵绵已经与曾小娥断了关系,但总归是曾小娥继女。我们只是找苏绵绵例行问话,公子若知道苏绵绵下落,还请告知。”
宋十安皱了下眉头,“苏绵绵的继母,死了?怎么死的?”
另一位衙役神色倨傲道:“官府办差,还要向你汇报不成?”
孙烨当即嚷道:“你怎么说话呢?我家公子乃忠武将军,问你话便老老实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