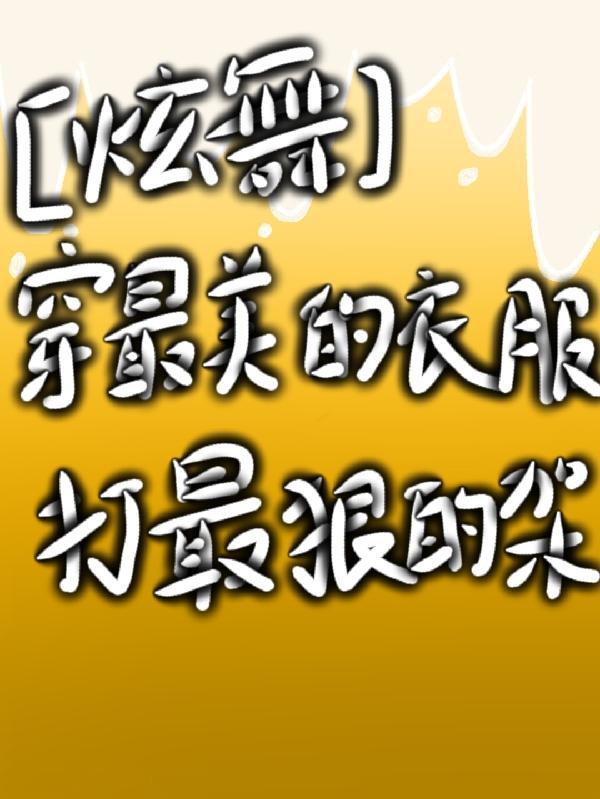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反映70年代爱情的老电影 > 第76章(第1页)
第76章(第1页)
提起来蒋国欢也有气,“住进来的哪里肯走,我爸也做不出赶人的事。”
等到了杨廷榕和葛斯熙的小家,蒋国欢里外参观完感慨道,“果然房子是新的好,看上去就整齐干净。不过你们家具也太少了点,等我回去找点好的送过来。”
杨廷榕张罗着泡茶,闻言回头笑道,“千万别!”
不是她想装穷,而是婆婆三天两头来视察,视察完就打听儿子的收入,屡屡借钱。
“你也太能忍了。”
蒋国欢和钱贵芳说。
“我还算能忍?”
杨廷榕自认属于敬而远之派,没看在葛斯熙的份上讨好婆婆。“开始最重要,我和婆婆在开始不亲近,后来也没特别改善,就……变成这样了,她说她的,听不听在我。”
“还好四喜丸子站在你这边。”
钱贵芳若有所思。
杨廷榕心里一动,“别说我了。你呢,和孙抗美吵架了?别瞒我们,桔洲这孩子担心你,跟我说了。”
钱贵芳淡淡地说,“他有两个同学来玩,嫌我和桔洲丢了他的脸。”
蒋国欢一拍桌子,“他自己算什么?小市民!他怎么嫌你,告诉我们?”
钱贵芳摇头只是笑,“提来干吗,何必添堵,我也是觉得他有段时间没见儿子,才带孩子进城。此一时彼一时,我不后悔,还要感谢他,有了他才有桔洲,儿子是我重要的宝贝。要不是怕儿子心里难过,他要自由我还他自由,反正对我来说,有他无他日子都一样过。”
蒋国欢说,“对。季东海不是对你有意思?孙抗美么,换掉他!”
“别开玩笑,我和季东海熟得像兄弟姐妹,没有其他意思。那时候年纪轻,我看了小说心里念着要谈恋爱,孙抗美给了我段美好的回忆,所以真的感谢他。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实在不合适。”
钱贵芳顿了顿,“我不后悔,我自己要的,自己承担。”
她说到这份上,杨廷榕和蒋国欢也无从解劝。两人选高兴的事聊,钱贵芳也跟着她们嘻嘻哈哈,度过难得的放松时刻。
过了两天,杨鸿生一个人跑到杨廷榕那,从里面的口袋里摸出封信,像笑又像哭,“你大伯伯没去台湾,在加拿大,给我们来信了。”
从前都说杨鸿生的大哥逃到台湾了,长期以来这也是杨鸿生被批斗的理由之一。
杨廷榕急急地展开信纸,信只有一页纸,开头是“鸿生吾弟如唔”
。仿佛有什么击中了鼻子,一阵酸楚冒上来,她努力睁大眼睛,不让水汽凝结成泪掉下来。
☆、生死
音信隔绝的十年,里面的每天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外面的牵肠挂肚,好不容易出现转机,杨鸿生的大哥杨鸿书寄出了投石问路的信。寥寥数行字,只说1967年后迁至加拿大温哥华,四子二女,除小儿子外其他儿女都已成家。
杨廷榕看信的时候,杨鸿生戴上眼镜,凑在女儿旁边又看了遍。一晃三十年,大哥本想把全家老小送去香港避难,但父母执意不肯离乡,说不管谁上台,总不会对风烛残年的老人下手。父母在,不远游,然而杨鸿书不是普通军官,实在不敢不走。杨鸿生挺身而出,说他留下来照顾父母。临别时杨鸿书给阿弟整整一盒金条以作生活之需,为生计故杨鸿生放款给人,没想到借条成灰。大哥身在香港,寄回大桶食物,植物油、大米、罐头牛肉、…寄得多,还是有些能拿到手的。直到1966年年底,联络完全断了。
泪水打湿镜片,杨鸿生摘下来,胡乱抹了两下,习惯性地看了看周围,用只有杨廷榕听得见的声音说,“别告诉别人,我连薇薇都没说。能回信不?”
虽说已经平反,但政策多变,风云莫测,这一通信,以后肯定是“里通外国”
的证据,他怕啊。可是不回信,说不定又会失去联系方式,他再也没有三十年可等了。
“爸爸,我来回,如果有什么事,我年纪轻,经得起。”
杨廷榕说,取出纸和笔,“爸爸,你口述我来写,有什么要告诉大伯伯的?”
杨鸿生摸着镜腿,仿佛有千言万语,可说什么好呢?过去的遭遇不能说,说也没意思,现在的境况也不能提,万一以小见大投射到国家形势,会给女儿招祸事。他想了又想,“就说,我们一切都好。”
是啊,还算好。
年初一葛斯熙和杨廷榕回杨家拜年,杨廷薇把姐姐拉进房,悄悄地说,“阿爹这几天很奇怪,莫名其妙地笑,又莫名其妙擦眼泪,问他有什么事,他不肯说。不会是姆妈同意复婚,他喜极而泣?”
杨廷榕哭笑不得,妹妹心心念念在这桩事上,不是跟她说别管长辈了吗。
年初二葛斯熙和杨廷榕作为葛成霖的代表,去探望山区的葛斯旭。他俩初四回来的,带了个16岁的孩子,那是葛斯旭继子中最大的。这孩子哭求着要去梅城,家里太苦,他想去好地方。
有什么办法,对这个口口声声叫她舅妈的孩子,杨廷榕只好尽量照顾他,让他住在自己的小家,教他使用新公房的厕所,教他说梅城话,带他上街熟悉环境。
杨廷薇背着别人劝杨廷榕尽快赶他回去,就说找不到工作。又不是亲生的,留在这,分明是想做跳板,以后阿二、阿三……阿小,早晚全涌来梅城,到时还不是她和葛斯熙受累。这帮小“赤佬”
既没受过教育,也不会任何手艺,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还不是白吃白住。
杨廷榕听她口口声声小“赤佬”
,忍不住又是暗暗摇头,自己的妹妹嫁了沈根根后,说出来的话也不像从前做姑娘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