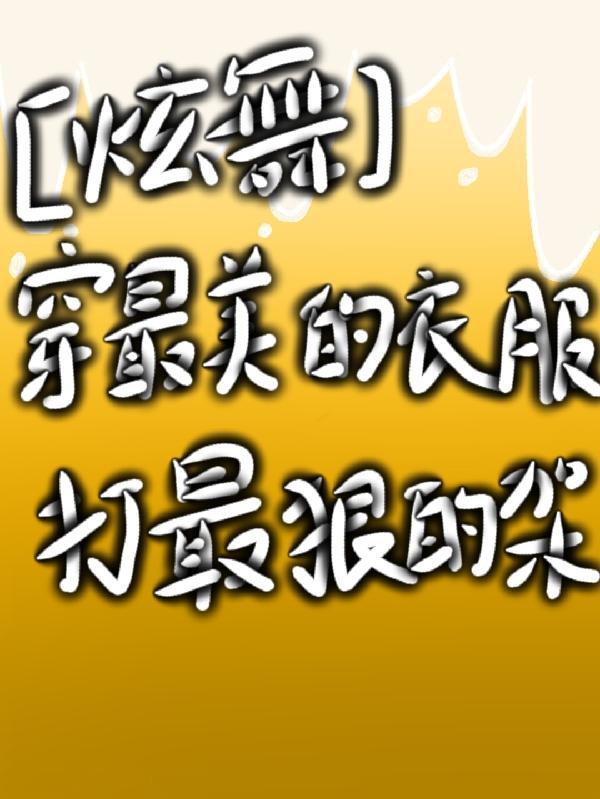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黎明复生 > 第78章(第1页)
第78章(第1页)
包装得太过鲜艳的糖,包装纸上甚至没有生产日期,一看就是粗制滥造的。毒贩往往会把真正的毒品伪装成各种各样的小包装,用以逃避警方视线。
江驰趴在床底摸了两阵儿,剩下的几颗糖也一并丢进了物证袋:“余芳毒瘾发作的时候说自己什么都没看到,一会儿说周善虐待自己,一会儿又说周善杀了王韬,虽然言语颠倒,但不一定就是信口胡诌,而且我看她的样子也的确是很怕这两个男人,要说周善和王韬没对她做过点什么,我倒是不相信。”
许愿没有很快搭理江驰,而是把物证递给痕检:“一会儿回去把物证交给毒品检验科,法医组派几个人去协助,尽量两小时之内拿到结果,审讯要用。”
“行嘞!”
“周善确实对她进行过虐待,”
许愿抱歉地偏头看了江驰一眼,继续接过江驰话音,沉吟道,“一年前他们两人离婚,法院审理的时候确认过余芳的伤情,后续的卷宗上也反映了周善家暴余芳这一点。”
那么余芳说的话,也确实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余生既然是余芳的孩子,”
江驰站起来,“他又是早产儿,后来余芳说周善让他生下孩子是为了卖钱换毒资假设余芳说的是真话,余生自生下来之后没多久就被卖掉,那么卖家是周善,买家是谁?”
“王韬,”
许愿下意识道,“陆风引之前说过,他捡到余生那年,来挂号的可疑男子使用过一名叫唐丽贞的女性的身份证——但你记不记得我说过,之前调查王韬的时候,我留意过他的人际关系,唐丽贞就是他的前妻,一名精神病患者,曾因虐待儿童致死而吃过官司,但”
许愿联想到什么,噤了声。
唐丽贞当时在儿童福利院工作,没有生过孩子。
后来她有一天突然打死了两个福利院里的孩子,被福利院院长告上了法庭。
“但却由于被告人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实施危害行为时缺乏辨认及控制能力,唐丽贞作为重度精神病患者,若将其投入监狱,可能使其疾病更进一步恶化,”
江驰轻轻地说,“我上网看了庭审现场的录像,当时唐丽贞的辩护律师是这么说的。后来法院二审的时候,判决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许愿颔首:“过目不忘?”
“我只是记性好,”
江驰温和地说,“队长,如果买家是王韬和唐丽贞,那我大概知道余生为什么会病成现在这样了。”
江驰的目光落在床头柜的软木板上。
软木板上用大头钉钉满了照片,走进一看全是女人和小孩的。
“队长,”
江驰拿起软木板,端详道,“这是余芳吗?那她旁边的小孩,就是余生?”
“看样子没错了。”
许愿指尖一张张抚过边角泛黄的老照片,突然在角落一张孩子的单人照上猛地顿住。
“队长?”
“等等,这张照片不对劲,”
许愿突然拿出手机对着照片按下相机键,打开地图捣鼓一阵,道,“这里这么多张照片,几乎全是小孩和余芳的合影,而独独只有角落里这张,是小孩的单人照,而且边角看上去很新,小孩也长开了,估计是后来拍的——为什么是单人照?”
唯一的一张单人照,一眼看过去,十分突兀。
大概警察当久了都这样,一点点不对劲的地方立马就能给你挑出来。
照片里的小孩约莫五六岁,穿着一身不合适的短衣服,脚上没有鞋,沾满泥巴的手里拿着个脏兮兮的果冻,不笑,就那么木讷讷地对着镜头,眼睛里也没有光。
和其他照片相比,小孩已经瘦得快脱相了,前后变化巨大。
什么样的小孩,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什么样的小孩,会瘦成这样,穿着不合适的短衣服,脏兮兮地站在镜头面前?
小孩的身后有个露出一半的建筑物标识,红色的广告牌,上面画着一颗星星。
而他踩在雪地里,光脚,小腿露出一半,已经发紫了。
照片背后则阴森森地用红墨水写着:余生六岁。
“被虐待的小孩?”
江驰猜测。
“嗯。一般父母不会禽兽到大冷天让自己的孩子穿短袖,而且还那么不合身,又是在雪地,天寒地冻谁受得了。”
许愿说着,目光放在一旁的其他照片上,“你看这些照片,镜头里的孩子都还算健康,余芳抱着婴儿,虽然说看得出来孩子营养不良,但也不至于太离谱不是吗?而在这张唯一的单人照里,这个孩子,已经完完全全瘦脱相了。”
江驰就着许愿的手看了一眼,忽然点了点照片右上角误入镜头的建筑标志:“这是哪儿?看着既不是滇城也不是钏岛。滇城的气候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型,南部州市基本不下雪,中部高海拔地区降雪较多——但我从小在滇城长大,却没见过这个标志。”
“我也是滇城土生土长的,这个标志明显不是滇城,”
许愿说,“照片估计是在北方拍的,那孩子小腿都埋进雪里了,我试试能不能用网络识图找到这个位置。”
“能行吗?”
许愿顿了顿,道:“找毒贩的时候试过,应该能。实在不行就把照片带回去交给技侦——但余生已经回来了,再精确的定位也不一定对案子有太大帮助,要破译照片地址,还不如直接找余生问问。”
江驰点点头。
“那个标志是红星福利院,现在已经逐渐取缔,”
许愿眉似刀削,冷静道,“早年全国各地有很多福利院都以它命名,大多都修筑在北方的偏远地区,目的是为了照顾留守儿童和失独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