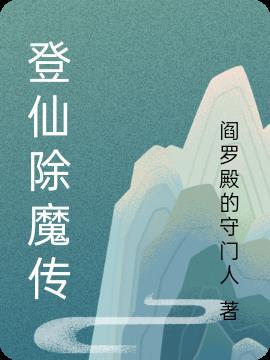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你快结婚了吧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容平虽然没有被掰弯,但确实在成年之前就已经不再能对女人提起兴趣,不仅女人,男人也不行……他是对人体,对人和人之间这种官能的刺激,已经产生排斥了。
这种反人性的训练体现在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的学业,他的兴趣爱好,他的交友情况,他的日常饮食,概莫能免。
容家的男人,就是那种孩子贪吃了一块巧克力,家长能买一车巧克力让孩子吃到吐吃到再也不想吃的类型…
熬到十六岁这一年,容平熬不下去了,他没有哭没有闹,十分平静地去找他哥,只说了一句话:“我宁愿自己不姓容。”
容和听完也很平静,不打不骂,在餐桌上想了想,合上报纸,点点头,答应了:“好。”
然后容平就冠了母姓,以“孟平”
的身份被扔到了山高皇帝远的叶城。
云城和叶城,在地图上能拉出一条长长的纵贯线。
容平一开始也会想,他哥到底是什么意思?驱逐不合格的继承人?或者,另一种变相的训练?
他想不明白,于是不再去想,在这个没有任何人认识他的环境里,他可以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
想麻木不仁就麻木不仁,想行尸走肉就行尸走肉,想随波逐流就随波逐流,想彻底沉沦就彻底沉沦……
他听见班主任在介绍他,说他的名字叫孟平。
“孟平”
“孟平”
,他自己在心里念了两遍,老实讲,他对母亲的印象已经很淡薄了。
打从记事起就只能在重大节假日一家人坐在长长的、连对面的人脸都看不分明的餐桌上吃饭,其余时间他都要跟着大哥学习……
印象淡薄如斯,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却依然觉得温暖,他木然地偏头看向门外,夕阳真好。
他的日子过得也很好。没有无休止的学习安排,没有无休止的人心制衡,想干嘛就干嘛,啥也不想干的时候就发呆。
这么悠哉悠哉地过了个把来月,突然就有了一个变数。
那是在学校食堂,苏轻尘被人欺负,白箴箴仗义相助那一次。
容平对女孩子们的斗争毫无兴趣,但是白箴箴一脚踹翻那张餐桌的时候,已经走出老远的容平被苏轻尘的笑声绊住了脚。
也许是被白箴箴那句“我要咬得狗爹狗妈都不认识狗儿子”
逗乐了,也许是被白箴箴浑身是胆的孤勇逗乐了,苏轻尘笑得十分开怀。
脚底是掀翻的餐盘,一地狼藉,身边是嘈杂的食堂,热闹鼎沸,她却笑得干净清朗,纤尘不染,容平回头看她笑啊笑,看着看着然后他就发现自己起了反应……
他见过太多种笑,清纯的,诱惑的,清冷的,妖艳的,谄媚的,倨傲的,不只是笑,她们做得更多更多,可是他除了与日俱增的厌恶与疲惫,早已不再有别的感触。
偏偏今天在食堂,只是看见她笑,他的身体就激动起来。
他将之归因于初初逃出牢笼的身心解放,很是不以为意了一段时间。
直到又一次,苏轻尘被老师指名在课堂上朗读课文,她的声音很轻,很柔和,跟她的人一样干净,毫无杂质,一望到底,没有杂糅任何隐晦的情愫,可偏偏容平又起了反应…
他把头埋在课桌上,默默思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于是开始观察苏轻尘,然后很快发现苏轻尘一直在偷偷观察他,就这偷窥水准,真的想不发现都难,浑身是破绽……
容平于是开始一边假装若无其事被她偷窥一边抽空反偷窥她,看来看去,结论是,苏轻尘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但就是特别能撩他……
她喝水的时候,纤细的手指头捏着玻璃杯,堪堪一握,仰脖子的时候下巴光洁,脖颈纤长,嘴唇上水色鲜亮,容平吞了吞口水…
她写作业的时候,脸颊边落下几根头发,挡住眼睛的时候,她就撅着嘴唇轻轻吹气,头发俏皮地飞起来,复又落下来,吹了几次索性不管了,发尾被她吃进嘴里,黏着唾液,缚在唇瓣上,容平手指头挠啊挠…
她走路的时候,整个人修长匀称,步态轻盈,柔软的腰身款款摆动,容平吸口气……
更不用说她每次念课文,每次同朋友说话,每次笑的时候,沉醉于她的音色在耳膜的鼓噪,竟至于连续好几天夜里梦见她在自己身下哭着喊“孟平”
,他几乎是当时就溃不成军,从梦里惊醒过来,总是满头满身大汗淋漓。
这样的日子开始变得磨人,比大哥的训练还要磨人百倍,他心里有些没着没落,不知道事情要往哪里发展,心里没个底。
放学值日那次,一发现就剩下她跟自己,他立马就想溜,可教室一个人也没有,她一个人要扫地拖地擦黑板擦窗户更何况还有天花板的大风扇要擦扇叶子。
他权衡了一下,实在没忍心走,只好躲她远远的,在角落里安静如叽地擦玻璃,他自然没注意碎玻璃渣子,他全副心神都在苏轻尘身上。
看她弯腰扫地露出后腰一小节白皙的皮肤,看她举胳膊擦黑板露出纤细皓白的手腕……容平渐渐有些神游天外,直到她突然跑过来攥自己的袖子。
正是夏天,容平穿的短袖,苏轻尘没得地方下手,只好小心翼翼用拇指和食指松松地捏着他一小节短袖袖口,这样一来,其余三根手指头就靠他的上臂很近。
温热的气息近在咫尺,容平浑身肌肉乱颤,绷到极致,终究是绷不住,扔了抹布,狂躁得不得了,原地打了好几个转还是不能冷静。
他没来由地生气,特别地生气,想也不想地就问出了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