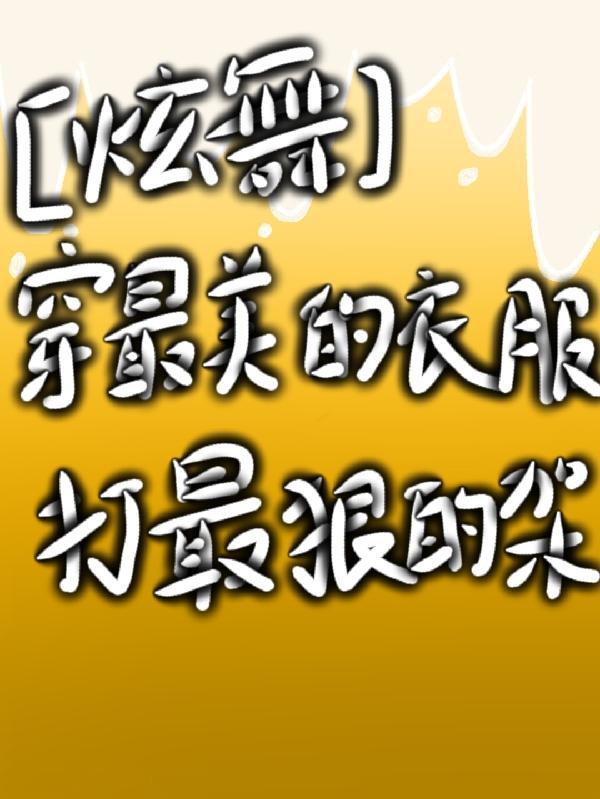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鬼灭之刃无一郎被腰斩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这人快死了。
容貌俊逸的男人,如水中冷月,见到时透无一郎过来了,手仍然放在那个鸟笼上,温雅开口道:“霞柱,您觉得养鸟最重要的是什么?”
时透无一郎只养过银子,但银子完全不需要他操心,他思考了一会,平静开口:“不准它们骂人。”
相原柊太听到这个跳脱到没边的答案,毫不掩饰他的惊异之情,后淡然笑了笑。
“这样吗?”
相原柊太徐徐开口说出了他的答案:“我倒觉得最重要的是给它们一个笼子,让它们知道,无论飞到了哪里,都逃脱不了这方寸之地。”
那段意味不明的话,现在看来可疑极了。
雀鬼——下弦——缪尔,越来越接近真相的猜测,如巨石压着人的胸膛。
到这一刻,时透无一郎确认了一件事,下弦四还没有死。
县志
时透无一郎在天亮前回到了相原家,袖口里还藏着那半截白骨。
绘里很害怕这个地方,但如同方才一样,时透身上那股稳重凛冽的气息,很像她的哥哥,让绘里产生了信赖。所以她缩在臂弯处,安心贴着。
这一次来,时透是直接翻墙进去的。从侧门悄无声息地一跃,就到了房顶,他在房瓦上疾走,寻找着蛛丝马迹。
厅堂那里很热闹,时透看到一群穿黑衣吊孝的人齐聚在一起。
那日之后,相原修到现在都还没有归队,据说是家中有亲人病逝了。
时透无一郎没有向那边去,而是潜入了书房。
书房里那个黑色的鸟笼还挂在那,只是颜色由原来的乌黑变成朱褐色,大开着的笼门,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人怀疑里边根本没有养过鸟。
桌子上摆着本摊开的县志,被窗外的风刮得卷起边角,时透无一郎走了过去。
原来森鸟县这个名字来源于一只鸟。在百年前的饥荒年岁,眼见着所有人都要饿死了。某夜森林里出现了一只神鸟,衔来了新鲜的肉类,才让少数人活了下来。
对那只鸟的描述不多,只说了其形似山,白羽红尾。那肉有人说是鹿肉,有人说是狼肉。
这里的人们对此感恩戴德,还专门把这个地名给改了,以作纪念。森鸟县的那些石碑,也就是那之后立起来的。
对着黄薄纸页上被勾画出的“不计量数的红肉”
二字,时透无一郎的手指点在那,隐约琢磨出了异样。
饥荒年间,怎么还会有这些。都到了要吃树皮草叶的时候,遍地生灵日子都不会好过。
如果是鬼那就是另外一番说法了。
果然,时透无一郎继续往后翻了几页,手一顿,眉尖微蹙。
这县志记载,熬过这场劫难后,人们发现县里的人有一半已经不知去向,凭空消失了许多人。
鬼叫人吃人,倒真是百年来都没有人发现的真相。又或是有人发现了,刻意隐瞒了下来。
时透现在很肯定,这里是不止一只鬼的。
当时入侵他思维,将他带到一人迹罕至山上后,那里见到的鬼,眼中明显是有下弦标志的,玩着那拙劣的模仿游戏,固执地要“妹妹”
成为缪尔。但他醒来后,斩下头颅的那只,眼中又没有字样了。
当时因为太过心急,在面对两张一样的脸时,把这个重要的线索给弄遗漏了。这才必须重新回来,解决祸端。
时透无一郎在书房又检查了片刻,这个书房的格局很简单,没有藏任何与鬼有关的物件。
在时透准备离开前,袖口里的绘里偷偷爬出来,掉在了桌子上,她用力抠着桌脚,在那里将木屑全部凿了出来。
时透无一郎时找不到一个精准的词来描述绘里的状态,在死物上寄托了灵智,也见不得太阳。把这里的鬼找出来后,她估计也就彻底身死了。
见再不阻止,整张桌子都要被凿垮了,时透想将她带走。但是绘里的劲很大,直接钻了进去。
厚重木桌看着结实,实际上是空心的。小鸟的骨架来去自如,就这样消失在桌子里。
时透无一郎瞬间明白了绘里的用意,他将书桌挪开,看到了那只神气十足的白骨,正爪踩着一张照片。
时透弯腰捡起,发现是一张双人合影。右侧的少年是相原柊太,左边的女孩脸被糊住了看不清。
将照片翻过,发现后面是有署名的,女孩名叫吉崎堇。
时透无一郎将照片收起,打算去其他地方看看。本想去那日休息的房间,但看到大厅聚集的人,时透还是换了个方向。
他想知道相原柊太是什么死的,这个男人连鬼杀队都要算计,他的死亡瞧着也会是场蓄谋已久的安排。
庭院三日前的战斗残局虽然已经被收拾干净,但因为这里的家主忽然离世,这座老宅上飘浮着混乱。
相原柊太的死成了森鸟县最大的轶闻,都盖过了辻村家那个籍籍无名的女仆。
鬼?鬼带来的利益没有死人诱人。
相原修看着还主持不了这个大局,他站在人群中间,目光穿过层层迭迭的人影,直达说话者的眼眸,紫色的瞳孔倒映出普通人的丑态,应付这些形如鬼魅、心思各异的外人,让他觉得很累。
那日发生了太多事,鎹鸦还送来了噩耗。伊织生死不明,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居然是他的至亲。
那些模糊狰狞的人脸不断在他耳边重复着:“好端端地,人怎么就会死掉,会不会是…,呸呸呸,瞧我这张破嘴。怎么可能会是报应呢。”
虚伪贯穿着这场葬礼,啜泣后的唾弃,全是冷血夺利。相原修脸色铁青,全程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