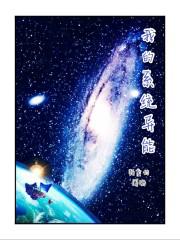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精神病怎么带孩子上学 > 第128章(第1页)
第128章(第1页)
校尉随机往台下指了几个人:“到时候死的人,可能是你,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还会传染给你们的家人,短短六日内毙命,全家绝户!”
此话一出,众人窃窃私语,皆是如芒在背,人人自危。
那校尉又道:“不只是京城,各地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毒人!你们想不想知道,这瘟疫是从何而来,那几十条人命,到底是因何人而死,又是谁要害我们!”
“想!想!”
台下众人振臂高呼。
校尉一手扶着腰间利剑,呵道:“如今,南北形式胶着,完颜单那贼子,霸占江南多年,江南人民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他为了攻入京城,培养毒人往京城投放,想不费一兵一卒取我等性命,光用疫病就把我们打垮,手段何其残忍,我们岂能坐以待毙!”
“乡亲们,你们说这个仗,该不该打!”
“该打!该打!”
台下数十人,异口同声。
“好!有我京国人民的血性!如今,我们与那乱臣贼子,已经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候,势必要收回国土,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还诸位安定的日子!
“现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正是用人之际,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各位老少爷们,各位英雄好汉,有谁愿意随军入伍,手刃狗贼,立下赫赫战功,流芳百世!谁敢为国死战!”
十九年前与刻矢国那一战,京国兵力大打折扣,这场宣讲的真正目的此时才显露出来,这是在征兵。不止京城,他们用同样的说辞在各地征兵。
如今当年的新生儿已经长成青壮年,京国忍气吞声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新一批的小兵成长起来,否则哪儿有兵力去收江南。
一听要自己上战场,不同于此前的群情激奋,底下的人瞬间鸦雀无声,也有几个热血翻涌的站上台去,雄赳赳气昂昂。校尉将他们一通夸赞,然后当场就被小兵领去了军营。
那校尉又道:“在场的百姓中,也有不少是江南避难过来的,有跟家人失散的,有没来得及把家里人带出来的,那狗贼害得你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回忆一下,你们在江南过的什么日子,现在又过得什么日子,是谁毁了这一切!你们想不想失散的亲人,想不想自己的家乡,想不想趁此机会返回故土,为亲人而战!”
流民之中的情绪明显比普通百姓高涨许多,有不少人都愿意入伍,左右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便不怕再失去什么,哪怕是去军营里有吃有住也好。真正受过迫害的人,有更强的凝聚力,更坚定的决心。
“走吧。”
姜蔚琬看明白了,便叫霍劭钦策马带他离开。
霍劭钦到了地方,在医馆外围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人埋伏。看来成相禹没有报复姜蔚琬的意思,的确,他若是想姜蔚琬死,不至于姜蔚琬当天还能从成府出来。霍劭钦这才把姜蔚琬放下马,随即调转方向与他分开了。
姜蔚琬刚一推门,便看到院子里都是人。他们看见姜蔚琬的时候,白虚室和林精卫立即快步上前来,孙保光拉着小满也走过来,裴钰双手抱胸不急不慢的跟在白虚室后面。
姜蔚琬的眼睛在这几个人当中略过一遍。这世上的亲情,爱情,友情,这几个人早就教给他了,什么叫舐犊之情,什么叫手足之情,什么叫两情相悦,他都能在他们身上看得清清楚楚,是他自己不学,主动把自己困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准确说是他一个人和一个死人,任何人都休想进入他跟他哥纠缠错杂的精神世界里。
如今,在周栾告诉了他真相,又经历了这许多以后,他才恍然大悟,但他仍然没有改变选择,只是由混乱的疯子变成了清醒的疯子。这世间的什么感情,管他正不正常的姜蔚琬都无所谓,他只想要偏执到疯狂的爱,就像姜蔚郅对他的那样,他觉得只有那样把他勒到窒息的感情才能叫爱。
“十七,愣着干什么,快进来啊!”
林精卫的声音还是像小鸟般清亮。
姜蔚琬听话迈了进去。
姜蔚琬在医馆住了几日,才发现京城里已经不复往日海晏河清,安居乐业的景象。集市上常常能见战马飞驰而过,原本嘈杂热闹的集市没有人说话,只有厚重的盔甲在马上颠簸,一声一声,听得人心惶惶。最恐怖的不是不知何时会打起来的仗,而是几不可控的瘟疫。
京城旁边的冀州,按街上的校尉所说,也如京城一般被投了毒人,两边作案手法如出一辙,都是街上莫名其妙出现一个暴毙的人,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上前围观,以此把瘟疫散播出去。其中因为围观得了瘟疫的那几个人,有一户的家属毫无症状,与健康人无异,却要被裹着面罩的官兵拉去尽数烧死,谁不怕死呢?他们费力逃窜,哭喊着救命,又被的官兵无情抓回,混乱之中,大人把一个五岁的孩子推出了官兵视野,那孩子逃了出去。
就是这个孩子,成了让整个冀州瘟疫泛滥的毒株。
这孩子自然是过不了多久就开始发病,然后死亡,但接触过这孩子的人,无一例外全部感染,然后人传人,感染者人数呈几何式爆发增长。
冀州百姓足不出户,全都躲在家中,老人在向年轻人交代后事,年轻人不知该向谁交代。每天都有官兵在到处抓人,焚尸场的大火日夜不停。
太阳照常升起
众多医师,大夫,江湖术士前赴后继,为这闻所未闻的病症研制药方,孙保光便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