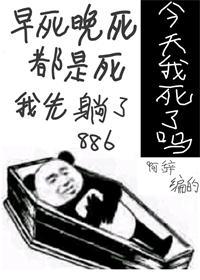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啊这里是规则怪谈 > 第45章(第2页)
第45章(第2页)
我干呕了几声,勉强摆手,知道不能怪他们。因为噩梦里有那么一段,好像是我总觉得有青面獠牙的怪物带着谜题要追杀我,我就一下子咬住了怪物试图厮打,心情悲壮异常。
现在我已经看到了,不说别人,野猫和小刘的胳膊上还清楚留有我的几个牙印子,下口非常狠。想必制伏我不难,难的是怎么避免我过度应激受伤。
等我完全把室内打量完一圈,一股渐渐浓郁的香味儿就在房间里萦绕开来。是小队长在地板上支起一口小锅,把牛肉罐头和泡面一起小火在煮,又撕了许多脱水蔬菜进去。
我肚子咕噜一下就饿了,差点口水没溜出来,赶紧让他记得再给我打个蛋。
小队长盯着还在突突冒气泡的锅,声音有点发沉,头也不回给我塞了一个鸡蛋。
“生的,你先拿着玩就当解馋。”
我点头,心情还是放松的,拿着鸡蛋在手里来回倒腾。
青白的冷光源下,就见其他人都看着我,神色无比复杂。
我顿觉不妙。
顺着他们的视线,我下意识反手摸了一下,就发现自己搭着毛巾的下半张脸和耳下湿漉漉的,全是新鲜的血。
老实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去看眼前的几人身上有没有其他伤,怀疑自己是刚才噩梦咬人的时候过于失控,上演了一出生化危机。
但接着,那种细细碎碎,好像下颔和耳后都曾开裂了许多小口子,缓慢渗透出血的迟钝痛感就无比模糊地到来,提醒我确实是自己受伤了。
“你一直在说梦话。”
严二掌柜说,脸色无比苍白,“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从说梦话开始,你就持续发烧升温和脱水。”
怪不得。是消耗过度了。
差点因为梦里不受控地解题,搞了一出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顿时有些心虚,好在他们都没有多说什么,很快煮好的豪华牛肉面就装在一个铝制饭盒里递过来,端到我面前。
吃饭的过程就不赘述,总之所有人都没打扰我,就好像我吃的是最后的断头饭一样。
呸,说到断头我就又想起刚才的噩梦,赶紧暗自说了几句童言无忌。
这一顿饭吃得异常快,跟饿了一个月差不多,满满当当的铝饭盒最后连滴汤都不剩。
看我吃完,又耐心等我缓了一会儿消化好,野猫就凑上来,用一种非常古怪的语气小心跟我确认:
“歇好没?”
啊?我一愣,有些迟疑点了下头。应、应该是好了吧。
不过说来确实奇怪,我这伤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我对受伤这种事实在没有多少经验认知,只觉得看着怪吓人的,但我居然还没断气。一开始在岗亭也是,我每次这个“轻伤”
的尺度都这么精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