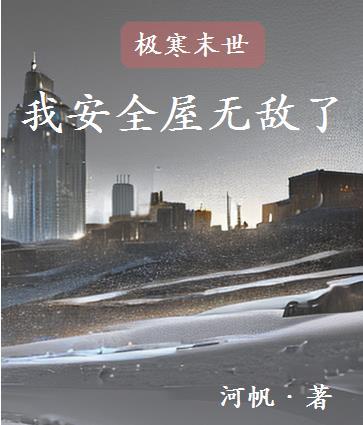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靖安县志介绍 > 第22章(第1页)
第22章(第1页)
想当初,他飞檐走壁从恶贯满盈的豪绅地主家中盗取了一袋金银,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个高楼,俯瞰那些助纣为虐的家仆为了追他在大街小巷上跑得满头大汗。
熟知半路杀出两个多管闲事的“程咬金”
,听了那些家仆大呼小叫的吆喝,便不明就里地参与对他的追捕,若只有黑衣少年一人,他也能逃之夭夭,偏偏还有一名蓝衣少女,似乎早已洞穿他的行动路线,他被堵了个正着,就停滞的几秒功夫,黑衣少年翩然落在他身后,带起一阵轻柔的风。
前后包夹之下,他只能束手就擒,做好了被押送官府、再伺机逃出生天的准备,不料,看上去非富即贵的少女了解事情原委后,竟主动放他走。
一旁的少年拧着修长的浓眉,“阿淑,对方报官了,你擒到了人又将人放了,县衙那边怎么应付?”
少女掏出一枚色泽纯正的玉质令牌,随意地掂了掂,“虽本欲低调行事,但这令牌又重又沉,一路揣兜里带着,不派上点用场,本公主岂不白白辛苦了?”
赵锋满脸惊愕:“公主为何愿意放了在下?”
“如今这世道,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劫富济贫,不合乎法理,但合乎道义,盗亦有道。”
杨淑话锋一转,“若让本公主发现你将这袋金银私自吞了,而非接济贫民,你要进的可不就是县衙大牢了,明白吗?”
赵锋抱拳作揖,“公主说笑了。在下赵锋,行不改姓,坐不更名,言出必果。公主今时之恩,日后定当涌泉相报。”
这日后一晃便是半年,发现蜀地的变故,他不遗余力地将消息带到京城靖安公主府。
“既如此,今日便让赵大侠心悦诚服!”
“好!”
赵锋话音未落,人已夺窗而出,谁知他虽先行一步,却未抢占先机,两人几乎是同时握住了凉亭上的避雷珠。
赵锋望着眼前锋芒毕露的少年,大笑道:“士别三日,果真当刮目相待,后生可畏啊!”
杨淑没空搭理不打不相识的两人,立即摆驾进宫觐见嘉和帝。
杨元对自己唯一的女儿向来纵容,知她不喜深宫高墙,便赐了一套京城中心的府邸,供她居住落脚。这日,她火急火燎地从宫外赶来,扰了他的午觉,他倍感不悦,依旧强压着怒气没有发作,杨淑并非一惊一乍的性子,这般匆忙,定有要事。
“父皇,蜀地疑似生变,据儿臣结识的江湖友人奔走相告,四川多名百姓罹患怪病,脖子肿大,体乏无力。”
杨淑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杨元哈欠打到一半,“什么?这么大的事,朝廷上下官员竟无一人禀报,蜀王也未发一言,你确定消息属实?”
“儿臣愿前往蜀地一探虚实。”
杨淑察言观色,补道:“蜀道口设了官兵,严控人员进出,儿臣那位江湖友人煞费苦心才将口信带到。”
杨元拳头紧握,青筋暴跳,“好啊,这是要一手遮天啊!”
杨淑再添一把火:“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然而近一年间向朝廷上缴的税额锐减,布政使说是蝗灾导致粮食歉收,真相如何,在消息层层封锁之下,又有谁知道呢?”
究竟是粮食歉收,还是那些本该上缴国库的税款都流入了蜀王府?
封疆大吏与亲王勾结,意欲何为?自立为王,密谋造反吗?
杨元面沉如水,古铜色的眼里却燃着熊熊怒火。
杨淑字里话间别有深意:“父皇,人心不足蛇吞象。同是皇室血脉,皇叔愿意一辈子没有实权地守着那数百亩封地吗?”
杨元铁青着脸,“朕知你已有计划,直说无妨。”
“回父皇,数月前,皇叔府上新添了个小儿子。”
此语如同一把利刀直直扎进杨元心里,而杨淑佯装没有看到杨元气得青了又白的脸色,径自说下去:“不如派新任的礼部员外郎苏旭代表朝廷送去贺礼和祝词,儿臣乔装随行,以免打草惊蛇?”
杨淑此行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谁让鸡先起了歹心!
杨爽笑脸相迎,还未意识到自己即将大祸临头,直至在苏旭身后的随行人员中瞥见一张半是陌生半是熟悉的脸,心头突了一下,回想起门客的提醒:“当今皇上缺子少孙,备受诟病,得知王爷您又喜添一子后,必定无比嫉妒和怨恨,怎会想着庆贺王爷呢?”
他那时光想着天子送礼岂有不收的道理,认为那门客纯属多虑。
“王爷这些年在蜀地过得太安逸了。”
门客长叹:“不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
他当即勃然大怒,将其逐出王府。
眼下却体悟他的分析条条在理,不由感到一阵后怕,冷汗浸湿了过分华丽的蟒袍,但为时已晚——
只见眼前白光一闪,一把长剑横空出世,一名鬼面红衣的少年身形如鬼魅,掠过人群,剑锋直指杨爽的喉咙。
变故发生得太过突然,王府的侍卫们慢了半拍,才想起自己的使命,陆续拔刀上前。
裴裕大喝一声:“谁敢动!”
手中剑刃又逼近几分,直接贴上杨爽的脖颈。
侧颈处冰凉的触感让杨爽浑身泛起鸡皮疙瘩,他干脆豁出去了,“尔等愣着做什么!还不擒拿刺……”
他忽地瞥见剑刃上沾了血——他说话间咽喉鼓动,擦破了皮,只是一点小伤,然而在高度紧张下,他本人竟以为自己被割破了喉咙,立即吓晕了过去,还得由裴裕架住他,才不至于倒在地上。
丢人!
鬼面都掩盖不住裴裕的一脸嫌弃。
杨爽虽已晕厥,但他昏迷前的那番话却给原先投鼠忌器的侍卫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侍卫们蠢蠢欲动,正欲群起而攻之。